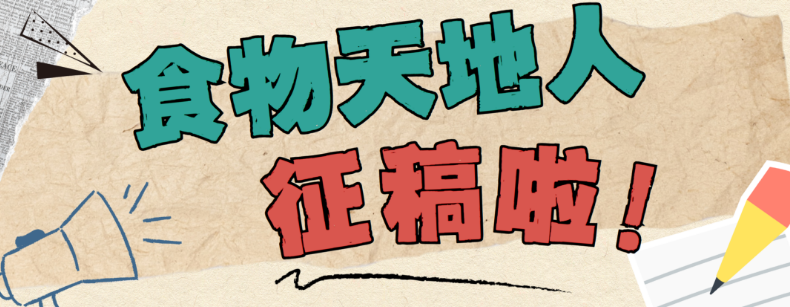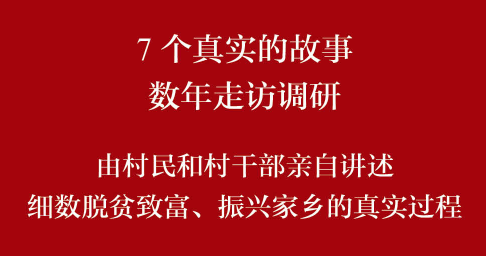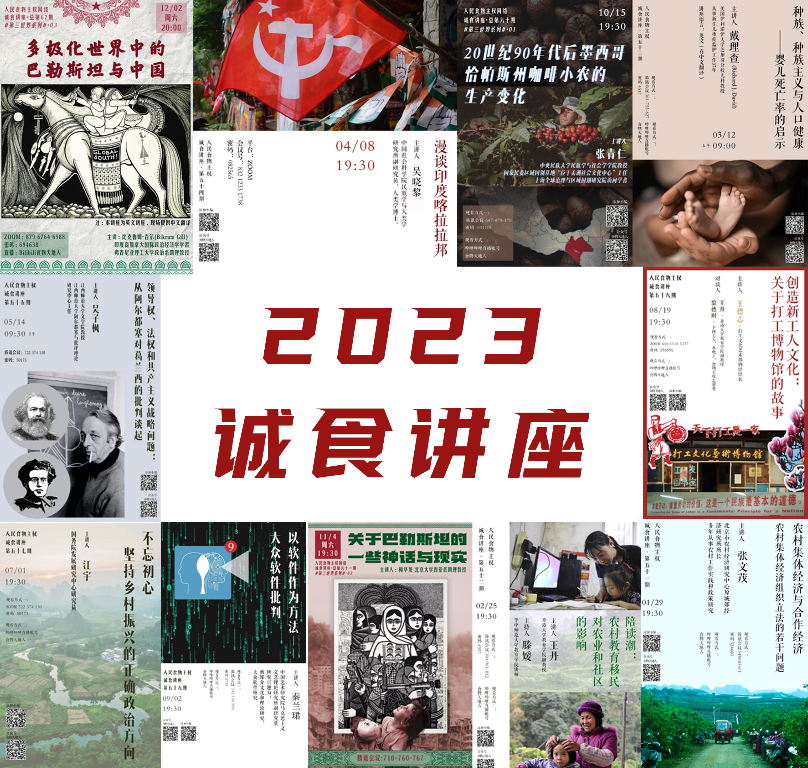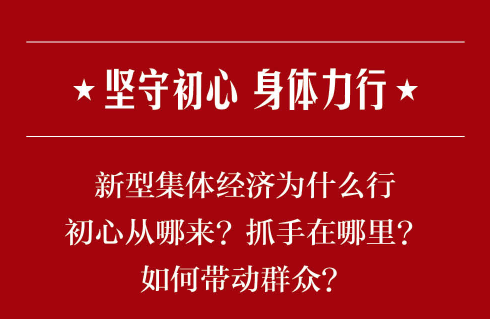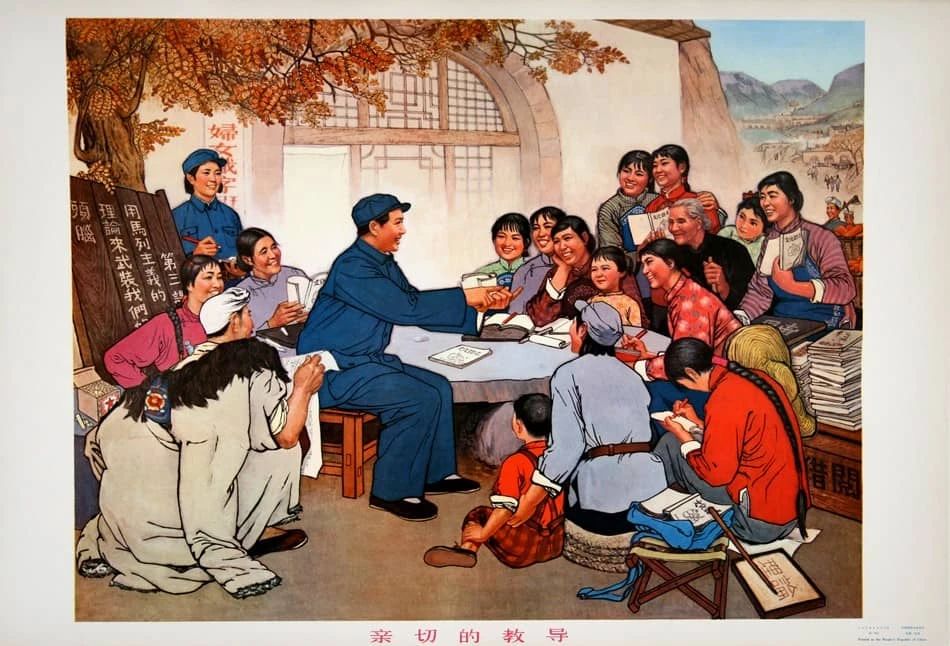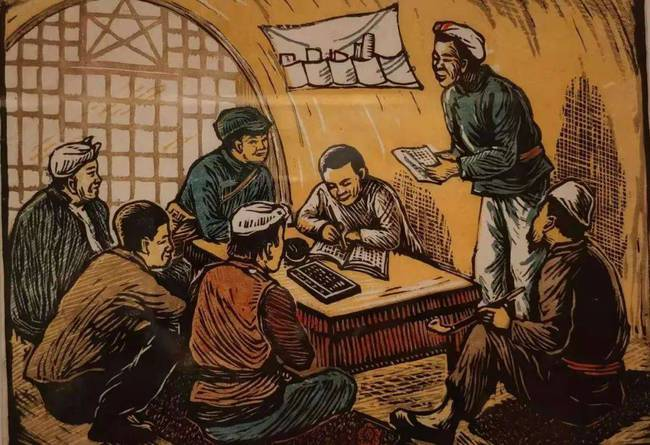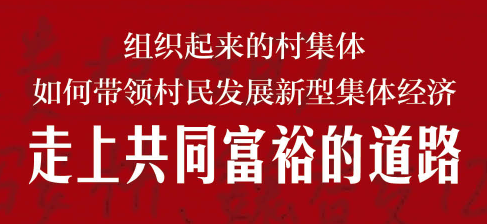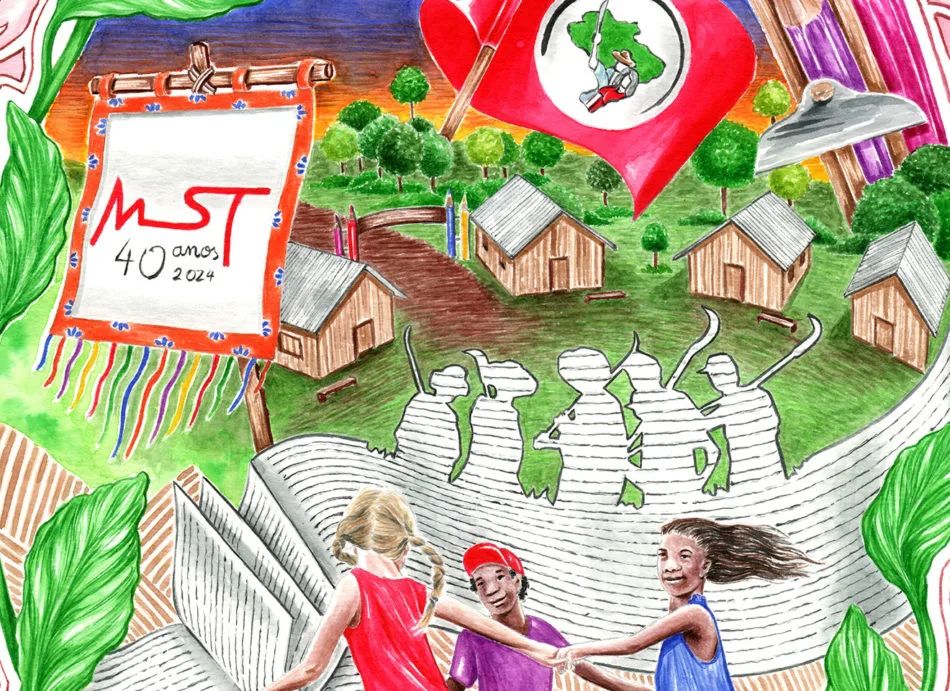土地二轮延包,“一延了之”恐伤农民利益
来源: 公众号“土生工作室”,公众号“三农庄园” 发布时间:2025-10-17 阅读:604 次
导 语
在以“大稳定、小调整”为导向的土地二轮延包政策即将推进之际,两份来自基层的实地观察报告,尖锐地揭示出政策落地过程中潜藏的现实难题。数十年乡村变迁浪潮下,农村耕地形态、土地承包关系与农业生产方式已发生深刻改变,一系列矛盾愈发凸显:土地确权证书登记的面积与边界,与实际耕种地块严重脱节;激光测量技术生成的“数字耕地”数据,与乡村实际可调剂的土地资源账不符;更关键的是,不少村集体因无机动地可分配,直接导致村庄内部土地承包不均。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呈现出与土地延包政策初衷相悖的现实矛盾。
现象背后,是农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重新调适。土地作为农村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既是农民维系基本生活的重要倚仗,也是村集体重塑与村民情感联结、保障乡村公共利益的载体。从江西村庄“5年小调整”的实践,到战旗村“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探索,再到永安村“调分红不调地”的创新,两位作者通过亲身走访挖掘的鲜活案例,从充分发挥集体统筹、组织作用的角度切入,为未来土地政策的优化方向与发展走向,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新思路。
作者|陈晶晶(土生工作室)、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博导,江苏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责编|上农食、侯Q
后台排版|童话
一、“大稳定小调整” 关于土地再延包的一封信
早上半睡半醒,记得梦里的意思是要打一个土地延包的报告,所以现在也不去吃早饭,先把这封信写出来。
我自己是2005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但对农业和粮食问题一直也不怎么重视。前面二十年一直看一号文件,看到反复被强调的事情:“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颇不以为然,认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是两件不怎么相关的事情。农民的主要收入是来自非农就业,对农民来说,乡村振兴最大的产业是“打工业”。十多年前,在教育部工作的姑父问土地政策的走势,是不是还有变动,有可能重新调地。当时我还不怎么理解,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山东老家的农民这么关注土地问题。
但是就像大家都看到的,2025年的一号文件是以“深化农村改革”为主题,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扩大整省试点范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承包地总体顺延、保持稳定”。
政策上为什么强调“大稳定、小调整”而不是“生不增、死不减”?这是我的疑惑。是因为很多地方都在表达了调整的需要?这就让我想起来这几年走过的一些村庄、乡镇的情况。原来政策与法律的规定跟农村实际的做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个差距一直存在,但不会被正式表达。我举几个我自己还熟悉的例子。
去年五一,成都战旗村的高德敏书记就兴冲冲地跟我说有个重要的事情跟我商量。我从杭州飞到成都。他核心表达的就是要给村集体新增的人口土地,给他们集体分红权。“地都没有,怎么能建立他和村庄的关系呢?”“最起码像在战旗村这样的城市郊区村,要给农民一块地,让新增人口能安稳下来。”怎么变呢?会不会影响其他农民的利益?
高书记的想法是基本盘不动,每五年搞一次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村里有去世或外嫁的,就把他们集体土地代表的分红份额腾出来,交给村集体新增的成员。如果新增人口比去世或外迁的人多,名额不够。剩下的人就排队,等下一个五年再发。是不是也有操作性?或许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更关注的是高书记提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从九八年二轮承包到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农地被征用或者通过“以租”代征的方式,转变为实际的建设用地。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厂房、公路下面的土地当成耕地,再继续承包给农户吧?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安徽小岗村。小岗村的“大包干”是改革开放重要标志。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召开座谈会,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2024年我自己两次在小岗村访问,得到的意见却颇为纷杂、多样。其中的一个小组,在女性组长的带领下,土地已经做了适度整合。组内劳动力统一调剂。农民们自己组织了合作社,土地既种粮食作物,也种经济作物,一亩地收益超过了2000元。而在另外一个小组,一个大户明确意识到土地是集体所有的。他排除了土地所有权在农户、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这两种看法,但是坚持认为现在没有必要搞土地依照人口重新作调整。“每个家里都有他自己分到的土地,并不是新生的人口就没有土地。”
这个看法跟很多搞研究的教授学者们的坚持是一样的。他们家人多地也多,又有人在政府上班,在大包干那年,一家子打的粮食比集体化时期全队的人打得还要多。而作为小岗村种田大户代表的程夕兵理事长的看法却又不一样。即便是大户,他认为时代在发展,改革要跟着步伐走。这四十年下来,村内不同的家庭人口变化太大。要给新增人口土地和分红。“生了不可以,死了可以拿。”这样的政策不合理。
他的这个看法让我想起来前些年广东南海碰到的一件事。有个城中村村书记跟我抱怨,他媳妇逼着他出钱给自家两个孩子“买”回了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分红权。广东佛山地区的情况跟其他地方不同。多鱼塘,农地使用权多在集体手里,定期搞发包。但他们那又认17年以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做法,认为“生不增死不减”是合理的。这样可以处理好集体收益分配的问题。
可长三角的情况跟珠三角好像又有不同。比如在苏州的吴江区和杭州的余杭区,土地所有权也都在村小组,虽然也多鱼塘,却没有搞定期发包。这块区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一直以来,小组内的土地都是定期调整的,同一个行政村内不同小组调整的时间和方式都不一定相同。
2018年,农业农村部原部长韩长赋在吴江开弦弓村调研。他在《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中写到:“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二轮承包以来,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可谓一组一策。有的“生不增、死不减”,一直没有调整土地;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动账不动地;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代替农民、替农民决策,更不能排斥农民。”
余杭区的永安村挨着杭州未来科技城,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们村2016年搞了全国第一个“田长制”,永久基本农田比例超过了96%。村里每三五年搞一次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这跟战旗村高书记的设想一致)。村里如果碰上征地,征地款都是归村小组集体所有。征地产生的社保名额由有需要的农户报名抽签获得。抽到签的农户还需要向小组缴纳一笔费用。从2019年开始,永安村各小组的地统一都流转到股份经济合作社之后,就不重新分地、量地了。调整的只是分红的份额,而不是调地。
现在永安村里的大部分土地由本村和外村的专业大户种植。通过土地置换,村集体专门为种植蔬菜的农民开辟了一些种植区,以便和由专业大户种植主粮的区域的分开。姚凤贤原来是村里的副书记。他对村里这几十年人和土地的变化很熟,认为这样的安排还挺好的、符合实际,有利于村庄的整体发展。比如村里的公路要拓宽,修路占的是大家的田地,就好协调。最多这几年你家多拿点租金,等调整后就又公平了。
以上的几个例子多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平原地区的个案。也不知道在山区和丘陵地区是什么情况。比如在贵州湄潭,他们当地农民的想法又是什么样的呢?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地条件下,经济发展的阶段又有不同,估计情况也各有差异。
就像在内蒙、新疆、西藏等草原牧区,人、草、沙、牛羊、生态是一个更脆弱的生态系统。很多的牧民脱贫也不久,他们从事畜牧业,生产方式跟精耕细作的农区以及农牧交错区差异就更大。草地的延包跟农地有什么不同,就更需要做认真研究。牧区跟牧区之间,可能也有不同的需要。
我自己是在全国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才开始认真琢磨农业和农地问题。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像很多外行的媒体工作者要追问“谁来种地”(这其实是个假问题),而是觉得乡土中国逝去之后怎么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个重大问题。在这个转折点上,它不再是像98年二轮承包那样,需要按照产权理论用土地延包三十年来保证农民的积极性。
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现在农民怎么看待土地呢?他们可能看土地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一种自己和集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能够带来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现在看来,不一定按照过去农业现代的思路,去着急推动土地流转,去切断农民和土地的联系。现在这个问题还看不准,得有耐心。就像今年的一号文件又强调的:“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
具体到土地延包这一紧要问题上,还是需要尊重各地的差异性,让农民和集体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更多的选择权利,通过自治和协商来调整人和土地,农户和集体的关系——即便它们看上去不那么符合政策,不那么符合书上讲的这个那个道理,不那么符合领导的意图,不那么让你、我或者别的人高兴。
文/陈晶晶(土生工作室)2025.3.2
二、关于农村土地若干问题的调查
暑假期间,我回到江西老家短暂停留了几天,除了陪伴老母亲,享受乡村的恬静生活,也趁机与基层干部和农民聊聊天。尽管算不上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乡村调研,但依然得到不少平时在书斋里了解不到的信息。考虑到有些信息对未来乡村的发展可能至关重要,因此记录下来,期待能够引起关心“三农”问题的同仁共同思考。
当前,农村土地二轮到期延包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按照中央的精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从逻辑上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只需要将现在的承包期限顺延到2057年即可。然而,尽管我们习惯于把土地视为“不动产”,但从1982年全国推广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第一轮15年承包期1997年到期,第二轮承包期30年也将于2027年到期。
经历45年的时间,当年分得承包地时还是15岁娃娃的我,如今都已经年近花甲,回到家乡再寻我当年种过的土地,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所以,无论是农村土地本身,还是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关系,一定存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变化,与村干部聊到这事,证实了我的猜测。归纳起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农村土地本身的变化
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耕地变少。江西大多数农村属于丘陵山区,农耕时代为了生计,山沟沟里只要相对平缓且有水源保障的土地都被垦成耕地,在实行分田承包的最初阶段,这些劣质土地也被作为耕地分到各家各户。后来国家出台“退耕还林”政策,加上农民外出打工不愿种地,很多山坑里的耕地就被“退耕还林”了,由此出现村庄总体上耕地变少的情况。我每次回家都要去屋后的山沟走走,看着当年我种过的土地,现在到处都是碗口粗的湿地松,感慨时过境迁;
二是耕地变样。传统的农业依靠人力畜力精耕细作,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如今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规模化耕作需要对土地进行“宜机化”改造,这就是“小田变大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近些年我回家发现,原来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被宽阔的机耕道替代,那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被规则的大块四方地取代,少了很多田埂,地块变得整齐划一,已经分不出我早前种的地边界在哪里,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三是耕地面积变大。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是,一方面随着村里山沟沟的耕地变林地,耕地减少了,另一方面村里的耕地面积却增加了。原因在于,“小田变大田”减少了很多田埂,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增加土地面积。此外,几十年前农村丈量土地的技术落后,靠拉绳测地,甚至对于山沟沟的耕地,面积多少基本上是靠农民的经验评估,所以那时候的一亩地不是严格的60平方丈,更不是精确的667平方米。现在都已经用上激光测量的高科技了,自然测量出来的土地面积,从数字上要远远大于从前。很多村庄现在的耕地面积,在新技术测量之后都要比原来多上数十亩甚至数百亩。
2、其次是土地承包关系的变化
农村土地自身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土地承包关系,这种影响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家庭承包地面积的变化。尽管国家政策在原则上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在现实中由于耕地数量本身在变,比如有些耕地“退耕还林”,涉及到的家庭就会出现自然的承包地面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家庭的重要性,农民要求实行动态调整,导致家庭承包地面积变化。
我调研的一个行政村,一共10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的情况都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至今依然坚持5年一次小调整的做法,只不过在调整过程中,增人所增的土地,一般都是村庄边缘的相对劣质土地,集中连片的大块土地保持相对的稳定。
二是家庭承包实际地块的变化。有些村庄尽管尽量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做到“生不增、死不减”,但这只是体现在土地面积的数量上,实际耕种的地块因为“大田变小田”的缘故,全部做出了重新的调整,我家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家兄弟耕种的土地已经不是我儿时耕种过的那些地块了,全部调整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相对集中连片承包。
三是家庭的土地承包关系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村庄,有的家庭增地,有的家庭减地,但与家庭增人与否无关。这是因为在1997年二轮承包时,农村种田还需要上缴“三提五统”,农民负担很重,再加上9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外出打工成为普遍现象,导致很多家庭不愿承包土地,甚至不少农村家庭把户口迁出退回承包地,一些山沟沟里交通不便,耕作条件较差的土地直接被撂荒。如果这时有人愿意揽包这些土地,既可以减轻村干部来自上级政府禁止土地撂荒考核的负担,同时也满足部分无法外出务工家庭想要多种地的需求。
在一个村民小组的调研发现,该村一户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户,包揽了村里所有村民不愿种的土地,这户人家承包的耕地占全小组耕地的1/10,同时也承担着这1/10耕地各种上缴费用的义务。还有的村民小组由于没有农户愿意揽包,只好由村干部承接那些当初没人要的耕地,当然也需要他们承担各种上缴任务。到农业税取消后,这些土地也自然归属于这些揽包的农户。
在农村,那时候迁出户口的农户其实并未进城,迁出的户口在自己的口袋里存着,成为“口袋户口”,农业税取消后有部分农户要求户口回迁,但也不可能再获得承包地了。因此从账面上看,这些村民小组内部的农户承包耕地是极其不平衡的,这是时代留下的烙印。
3、再次是土地生产方式的变化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早期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全称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土地要联系产量,“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所以,农户承包土地是需要直接经营的,承包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很多农民进城务工,留下的老人、妇女、儿童无力耕种承包地,因此有些留在家里的农民为了增收,就以“代耕”方式流转土地集中耕种。
那时候的土地流转不仅不需要流转租金,甚至还可以得到一点“代耕费”,因为耕种者需要承担各种税费负担。“代耕”方式的盛行,意味着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但这种分离是不彻底的,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户“代耕”流转需要每年一次反复签约,流转可能随时终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国家种粮补贴政策的出台,承包农地对农户来说成为一种权益收益,现在的农村“代耕”依然是主要方式,但已经由转出方支付“代耕费”变为转入方支付“流转租”,大概每亩在120元左右,国家粮食补贴归承包户,种田直补归种植户。一个村庄里的耕地大概只有2、3户种田大户在耕种。
以我们村的情况看,因为水土条件较好,种一亩地两季并算,能够有1000元左右的利润,村里有户农户种了100多亩,一年的种田收入超过10万,土地变得稀缺起来,再也没有撂荒现象出现,反倒是找不到地种成为种田大户的心病。
二是农业分工程度不断深化。种田大户种植面积的扩大,自然不能再靠人力畜力,也不能事必躬亲。因此,插秧、喷农药、收割等服务外包在农村已经十分普及,农业再也不像之前由自己从头干到尾了。我看到吉安市的无人机农业服务公司到村里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深深意识到农业分工已经到了高级阶段,这意味着将来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将会不断固化,甚至还会衍生出更多的权能。
面对上面的这些变化,在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落实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需要对此有充分的估计:
一是土地确权后遗症的影响。按理说,第二轮承包延期要在原来承包的土地基础上进行,但调研发现,第二轮承包期间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确权证书上记载的承包土地面积,与农户实际承包的土地在面积上和地块实际的空间“四至”边界上都存在极大的出入。
在面积上,有些农户确权证书上记载的承包地甚至与实际承包地的面积数量相差数亩地之多;在空间“四至”边界上,很多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地块在“四至”边界图上显示为同一个地点,形成相同一块地有N个户主的情况,这可能在二轮承包延期落实上,产生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另外,由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很多村庄不同程度进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原来的地块在“小田变大田”过程中“四至”边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承包延期如果要做到准确落实承包地块的“四至”边界,就需要重新变更“四至”边界,这事实上就需要在第二轮承包期结束后把土地打乱重分,但这又与国家政策要求不一致,这个矛盾的解决是需要时间和人力物力的投入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二是土地面积账实不符的影响。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的时候,土地是一块一块进行测量,再“肥瘦搭配”分到农户家庭手中的。尽管那时候的丈量方法落后,但每家农户承包多少面积和地块在哪里是非常清晰的。现在由于土地的变化,由第三方机构重新测量农村土地面积时,并不是采用逐块地块测量的办法,而是相对完整的地块整体测量。
众所周知,丘陵山区的农村土地没有那么规整,田地中间存在水沟田埂甚至土坡,因此,原来一块一块耕地测量的面积,与现在整体测量的面积必然出现差异,新测量的面积要比原来逐一地块面积相加的总量大得多。
在某村庄的调研发现,新测量的面积有2600多亩,而农户实际承包的面积加总只有2400多亩,因此多出200多亩只有数字而没有实际地块的“耕地”。按照国家现行的粮补政策,这些数字上的耕地,对于村集体和村民小组来说,是可以得到一些转移支付收益的,也许它的存在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如果把这些只存在于账上的耕地面积作为村集体的“机动田”,在需要对农户承包地进行微调时,是根本拿不出土地来满足农户新增土地要求的,这对二轮承包延期的落实也会带来新的矛盾。
三是土地耕作方式变化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土地承包的早期阶段,由于还属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加上繁重的税负,很多耕作条件较差的土地被农户弃耕,有些弃耕的土地被当地另外一些愿意耕种的农户揽包,由此造成村庄内部承包土地多寡不均的失衡现象。
随着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现在大多数耕地的耕作条件有了很大变化,农业分工的深化使耕种土地的收益不断增加,原来“弃耕”的农民现在却想找地种,对历史原因形成的耕地承包多寡不均现象,出现重新分地的呼声,但这与国家的延包政策不符,如何解决这类矛盾,仅仅依靠村干部是难以解决的。
短短几天时间的乡村调查,发现的问题可能仅仅是个案,但毕竟这些现象是存在的,因此需要引起“三农”学者的广泛关注,也要政府部门在第二轮延包工作实施过程中引起重视。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倾听农民及基层村干部的呼声,不能简单一刀切。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江苏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公众号“我家农村的”,2025-03-02;公众号“三农庄园”,2025-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