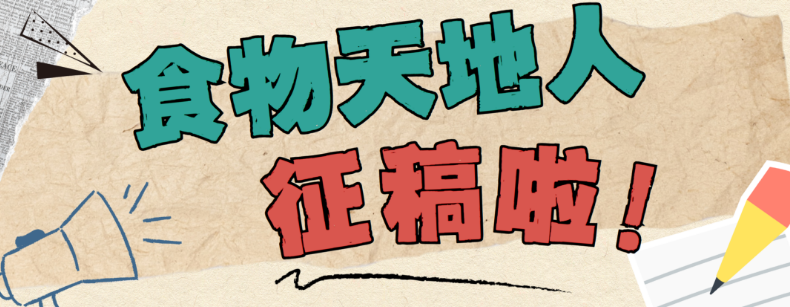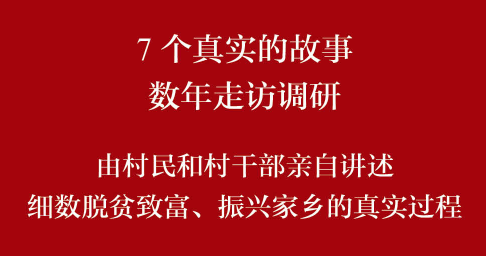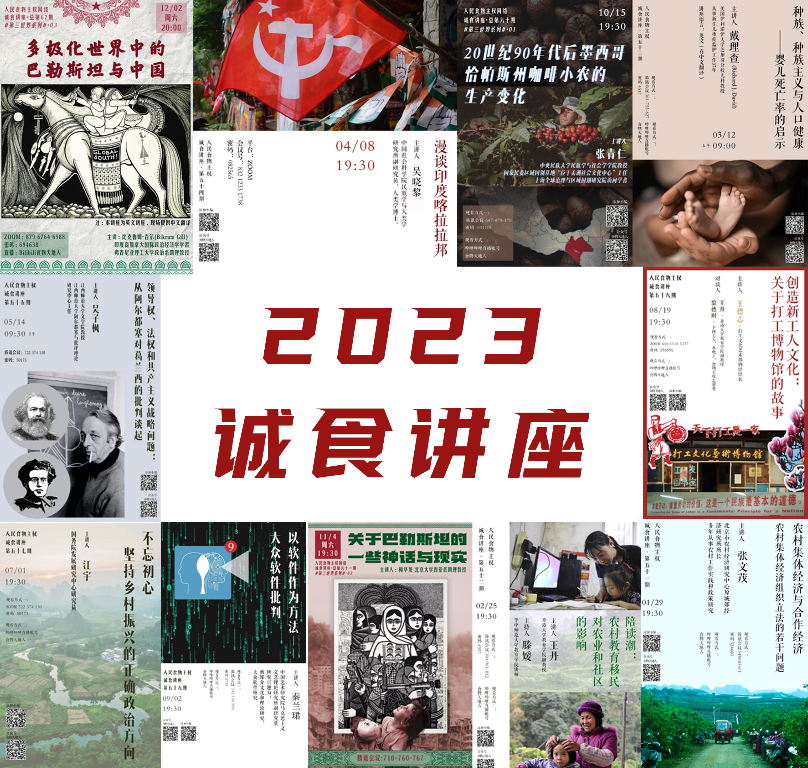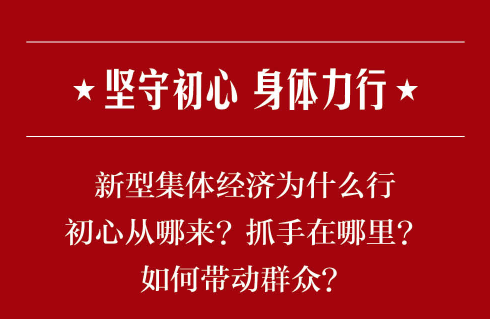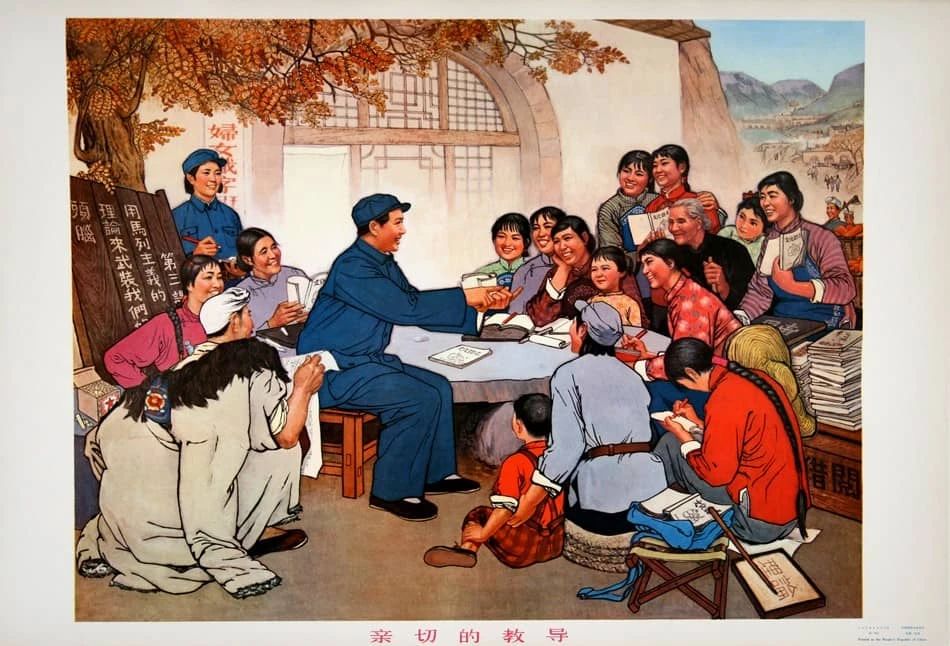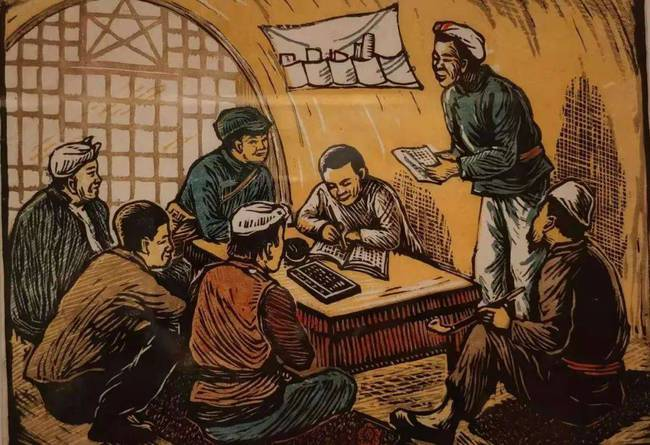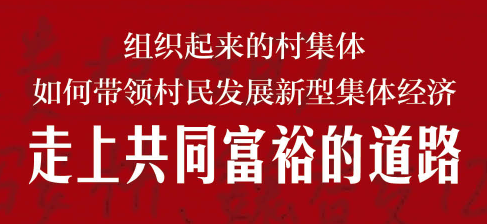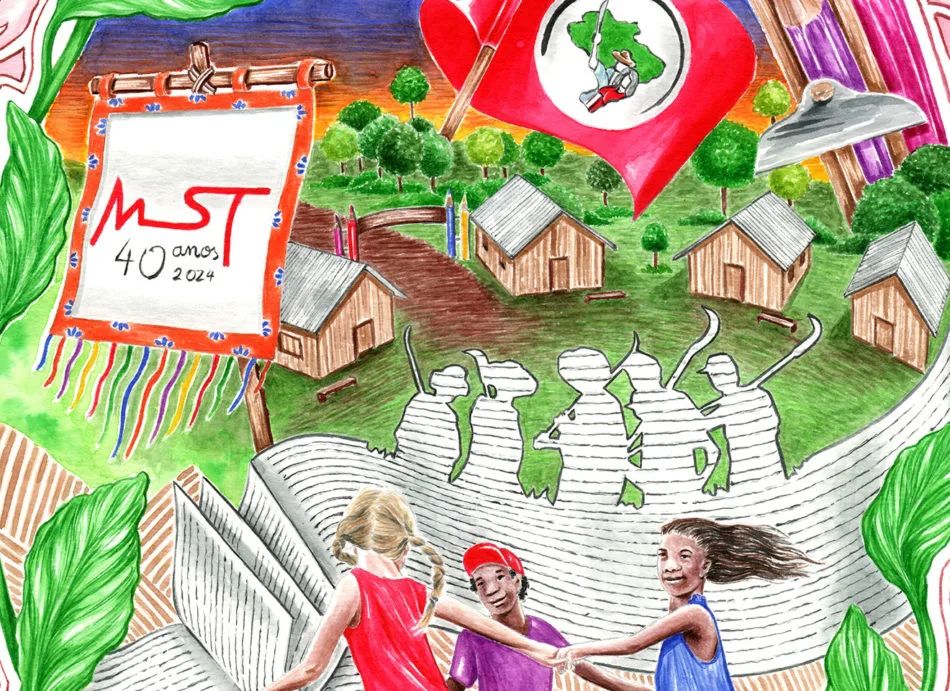“我们为银行放牧”:牧民在教育和发展之间的两难抉择
来源: 游牧研究-CPS 发布时间:2025-04-26 阅读:1030 次
导 语
在蒙古国,牧业支撑着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计,但现行的教育体系正在深刻改变这一传统生计模式。
为了让孩子接受正规教育,牧民家庭被迫分离——部分或全部成员迁至学校附近的城镇,以便为学龄子女提供住房、生活照料和学习支持。这种分离不仅割裂了家庭结构,还导致牧区劳动力短缺,并加速了年轻一代的“去牧化”进程。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牧民后代逐渐成为专业化、技术化的个体,与季节性放牧的知识和技能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为了负担教育开支,牧户不得不抵押牲畜获取贷款,并雇佣牧工维持冬季放牧,从而推高了生产成本,加深了对金融体系的依赖。
最终,许多牧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悖论:他们仍在放牧,却已沦为“为银行放牧”的人。
作者 | PASTRES
转载编辑 | 侯丹 米玛
排版 | 侯米
正文
“过去,孩子们通常在七八岁时开始上学。如今,甚至两岁的孩子也开始上学,母亲会带他们去城镇中心(居住在那儿)。然后,在蒙古包(传统游牧民居,蒙语称‘ger’)里,男人独自一人。独自醒来,带着羊群外出,返回时又是一个寒冷的蒙古包。如果是我…在我看来,我希望能够稍微改变一下这个教育制度。然后,所有这些年轻人现在都搬到了城镇中心。他们增加牛羊数量不是为了改善牲畜的品质,而是为了屠宰其中一半来买一套市中心的公寓。”

在2012年至2014年间,我们在蒙古巴彦洪戈尔省与移动牧民共同生活和工作时,经常会听到他们提到学校如何成为改变他们的家庭组织、劳动力和财政安排的原因之一。我们观察到,牧民在偏远的季节性牧场照料牛羊的同时,还需为在行政中心上学的孩子提供住房、生活用品和关照。这些涉及到了复杂的家庭和劳动力的安排,由此催生了新型的牧民生活方式。
诸多关于教育与发展的最新研究指出,针对以流动为主的牧民的正式教育政策存在诸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包括固定化的学校位置、家庭教育与学校系统化教育的混淆,以及一种将牧民生计视为低于“现代”受过教育生活方式的取向。
蒙古有着悠久的国家主办教育历史,这段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正规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普及到大多数地方和人口。自社会主义结束以来,乡村人口的入学率仍然很高。2012年,巴彦洪戈尔省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8.8%,高于全国的95.2%(蒙古国国家统计局2013)。蒙古牧民对教育需求强烈的一个标志是他们在子女教育上的巨额财政投入。研究发现,仅2010年,牧民所贷个人贷款的67%用于了教育投入。
牧业支撑着蒙古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计。2013年,蒙古27%的家庭被登记为是全职牧民(蒙古国家统计局2013)。牧业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9%,并塑造着诸多公民的文化身份。而且,牧民作为全球重要草原生态系统的管理者身份存在。
自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蒙古人口面临着显著的收入不平等和不确定性。尤其是牧业,作为在不稳定的商品市场、通货膨胀和基本食品价格波动的背景下一种稳定的非现金投资和食品安全形式,并且许多城市居民依赖于牧业食品的供应。尽管牧业在蒙古国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却对牧民生计构成了挑战。
为了确保孩子的教育,牧民家庭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提供住房、课后辅导服务、校服购买、食品和学习用品等等。政府政策,包括新近降低的入学年龄、学校和服务集中在半城市和城市中心以及宿舍的监管不足,给正式教育的获取增加了额外的难度和障碍。
对于许多牧民家庭来说,为孩子获取教育意味着家庭中的某些或所有成员必须定居在学校附近。在蒙古牧区,这种定居通常是通过“家庭分居”实现的。家庭通常将住所分布在牧场地点和学校地点之间。这一做法催生了通过年度贷款进行的新型财产投资和融资。很多牧民提到说,这种分居妨碍了孩子们学习季节性放牧知识和技能。此外,当家中的女性和孩子们迁往学校附近后,家中的男性则需要待在冬季牧场,因为劳动力短缺,男性需要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照料牲畜,这不仅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福祉,也威胁到了牲畜的福祉。
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牧民描述了在照顾羊群、维护对牧区资源的权利以及同时为孩子提供教育方面的困难和担忧。而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提倡牧民教育公正的观点,即只有当教育的提供“而非与已具生计可行性的牧民生计竞争”时,教育公正才能实现。学校的可及性和关于教育的叙事往往在学术辩论中被忽视,然而这些在家庭决策、牧民身份和随后的生计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教育作为一种有争议的资源
已建立的社会学批评已表明,正式教育在与国家项目和日常社会关系相关时具有固有的政治属性。很多学者指出,教育政策和教育机构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立场强调了学校教育实践中往往具有排除性,这与国际发展框架将教育视为一种内在有价值的社会公共物品和中立的社会干预的观点形成对比。
正式教育可能具有矛盾性,因为它既可以促进个人成长,又可能通过对某些文化形式、知识、技能、风格、工作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在教育和非教育成员之间造成新的社区分裂。莱文森和霍兰德(Levinson & Holland,1996)关于“教育人的文化生产”的研究重点讨论了个人如何在教育机构中创造性地导航,并突出了通过学校教育和个人选择来利用、拒绝或模棱两可地表现“受教育者”身份的文化价值。学校外的竞争性道德框架,如性别角色、乡村生计和其他形成主体性的实践,可能与教育身份发生冲突,并涉及地方性、劳动价值、社会角色、地位和文化资本等方面的谈判。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及其后教育经验,推动了教育作为有争议资源的辩论。在Jeffrey(2008)的研究中,印度受过教育的年轻男性在没有额外的社会网络、地方联系及其他强制手段动员资源的能力的情况下,难以从教育资格中获得预期的收益。这些案例展示了在资源获取的其他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年轻人的教育身份所面临的局限性,表明教育的价值不是内在的,而是社会生产的。尽管这些研究集中在印度的个体在教育后空间中的经历,但它们也指明了教育在结果上的矛盾性。
全球范围内,从事牧业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教育作为有争议的资源。与南亚、中东和非洲的牧民合作的学者展示了学校环境如何在定居社区和流动社区之间产生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立,反映出国家政策对流动牧民生计的主流叙事和态度。历史上,国家一直将依赖于社会技术系统以应对动态干旱环境的牧民视为与现代社会对立或在其外部的存在。这一意识形态基于“缺陷话语”,并继续影响着许多国家对牧业、牧区的政策,这些政策将流动性为主的游牧视为经济上不理性或环境破坏的根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蒙古国总理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在2001年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呼吁结束牧业,并在三十年内将90%的人口迁移到城市。恩赫巴亚尔通过1999至2001年期间12,000个牧户因严重干旱和冬季寒冷造成的牲畜死亡事件来质疑牧业的可行性,并以此来支持他的政策。他的批评没有承认政府在加剧这场灾难中的作用。此外,在蒙古,一些牧民将自己的工作视为“非专业和熟练性的”,并将自己的主观性视作“没有文化”。
我们观察到,无论是牧民还是非牧民,通常都认为bolovsrol(正规教育)是区分牧民和非牧民的一个特质。牧民们认为,正规教育有助于形成soyoltoi(有文化的)和meregjiltei(熟练的)世界观。在这一社会话语中,无论是牧民自己在自我的评价中,还是非牧民的评价,牧民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和缺乏技能的。正规教育被视为一个转型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成为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个体,从而与从事乡村生计的人区分开来。牧业生计具有多样性、理性,这种生计涉及高技能劳动和专业性知识,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引入新技术和信息。
因此,像Dyer这样的学者挑战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宣言》下实施的为牧民提供国家教育计划的假设。Dyer评估了将牧区儿童从社区学习和社会化的地方移除所带来的生计矛盾性影响。一方面,儿童获得了作为倡导牧民权利、资源和土地的关键工具的识字技能;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使儿童无法学习牧民生计所需的技能,并且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牧民生计的“缺陷话语”。此外,Dyer(2013)指出,在印度,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牧民身份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学校教育一直在推动一个观点,那便是,受过教育的人不(会)从事牧业。
在我们的研究中,教育的矛盾性具有多重空间特征,甚至在孩子获得教育资格之前,这些矛盾就已影响到家庭。牧户在牧场和定居点之间的分裂、劳动约束以及分离带来的情感压力负担,使得在季节性的草场生活变得不吸引人且存在争议,尤其是当男性在学年期间留下来照顾牧群时,我们并不是认为教育缺乏价值,而是认为在特定的治理和制度框架内追求教育可能为从事牧业生计的家庭带来新的困难。
二、治理与教育基础设施的变革
教育在蒙古社会中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正规教育在1204年成吉思汗采用回鹘蒙古文后得以确立。之后,忽必烈汗创建了一个帝国范围内的学校体系。到十六世纪中期,教育在佛教寺庙中进行。寺院教授藏文和蒙语。在清朝(1636-1912)期间,学校用于培养地方行政人员,尤其是在偏远地区。Marzluf(2015)认为,社会主义之前的家庭教育实践主要依靠非正规家庭教育,通过游戏、诗歌、歌曲、从藏文到蒙文的翻译文本、家谱图表和仪式文本等方式进行学习。自192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强制教育始于1950年代,国家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相当可观,建造了学校和学生宿舍,尤其是在行政中心和工人协会及集体组织旁边。牧区的孩子住在学生宿舍里,这些宿舍融入在社会主义乡村经济体制中。即便在今天,学生宿舍仍在被评为“最佳实践”,尤其是在对游牧民族教育的应用方面。虽然社会主义体制在提高国家识字率方面极为高效,但仍不清楚学校宿舍制度是否可以被评估为蒙古牧民教育公正或最佳实践的一种形式。
随着苏联解体,1990年代初期国家对教育的资助急剧下降,这导致许多乡村学校破产,教师未能得到薪资(很多只以粮食或肉类作为报酬)。这种背景下,牧户承担了许多教育成本,如支付教师工资和学生住宿费用等。这些新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因为在此期间蒙古国还经历了广泛的失业潮。许多新失业的蒙古人回到乡村从事牧业,虽然这保证了基本的生计安全,但也导致了额外的现金短缺现象。这一期间,净入学率从1999年的97.3%下降至2002年的88.5%,但到2012年,入学率恢复至95.2%(蒙古政府2013:61)。学校宿舍系统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而陷入困境,牧民们也不愿让孩子住进宿舍,因为宿舍常常与低质量的照料和差劲的学业表现联系在一起。由于牧民们没有其他住宿选择,他们必须安排自己的住房靠近学校,这导致了家庭分裂、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2012年至2014年间,我们在蒙古西北部巴彦洪戈尔省的古尔班布拉格、巴彦布拉格和乌勒吉特县开展了关于牧民工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巴彦洪戈尔省有二十个苏木(县),是蒙古国牧民和牲畜最多的五大省份之一(蒙古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每个苏木都有一个行政中心,通常包括围起来的住宅区、一个小学和中学,有时还包括一所高中,以及当地政府办公楼、基础医疗设施、银行、商店、修理厂和至少一个加油站。巴彦洪戈尔市是主要的市场和交通枢纽,也是多所高中的所在地,以及一些职业学院和一所大学。许多学生在县级学校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学校通常开设至八年级或九年级。因此,一些牧民将孩子送到超过200公里(大约一天车程)外的省会,来完成中学的最后两年(十年级和十一年级)。我们与全职牧民进行了75次半结构化访谈,还访问了当地居民,在与家庭共同生活和工作时收集了材料。分析的材料还包括县级会议的观察记录、季节性营地的地区地图,以及多次访问巴彦洪戈尔省省会和乌兰巴托的家庭及其扩展家庭的家庭访问。
三、牧民家庭的教育资源与家庭分裂
如前所述,牧民重视教育,并选择积极让孩子进入正规学校。由于距离学校遥远和不好的交通条件,接受学校教育意味着要住在离学校较近的地方。为了满足这一要求,牧民根据家庭规模、在校儿童人数、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牲畜种类等因素,采取不同的家庭分裂模式。在我们展开研究的地点,Bag(乡政府)表示,约50%到60%的家庭在学年期间分裂。牧民们表示,在冬季,牲畜通常由年长的男性照看。一位乌勒吉特的牧民解释道:
“在乡下,只有大约六十到七十岁的老人留下来照看牲畜。你看看,年轻人夏天回到乡下收奶,秋天因为孩子上学和其他事务,他们把牲畜留给老人,自己去县城。”
我们发现,Bayanhongor地区的家庭分裂有四种基本模式,这些模式清晰地显示出家庭空间组织的变化与儿童上学之间的联系。
在巴彦洪戈尔,牧民家庭的学龄儿童通常在每年六月到九月的夏季与家庭一起在牧场生活。学年期间,从九月到六月,孩子们会从牧场搬到学校所在的苏木或省会。如果扩展家庭成员没有住在学校附近,牧民们会建立第二个住所,将孩子们安置在那里,孩子通常会和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一起生活。由此产生的家庭分裂,通常会将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独自留在冬季牧场照看牲畜,或者将牲畜交给朋友、亲戚或雇工照看,而全家则搬到行政中心,或者两者结合。这种变化与牧民孩子进入小学密切相关。
乌勒吉特的牧民Purev和Bataa,分别为30岁和29岁,他们有两个年轻的女儿。大女儿开始上幼儿园时,他们便计划在学年期间分开照顾孩子和生活。Purev是巴彦洪戈尔戈壁地区一位成功的骆驼牧民的儿子,家族继续经营着几百只骆驼。Bataa解释道:
“很快,我们中的一个人会去省会,我的女儿要上学,而我的丈夫则会独自留在这儿照看牲畜,而我去省会照看女儿。我虽然希望留在一起,但不得不去,因为我们的孩子要上学。”
Bataa计划在九月到六月期间离开,每当学校假期,比如农历新年时,她会回来帮忙照看400只山羊和70只羊。她形容与丈夫和牲畜分离的这段时期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描述困难或负担沉重的口语表达。尽管这个家庭住在乌勒吉特县,他们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到省会的学校,而不是乌勒吉特县的学校,尽管乌勒吉特更近。在访谈中,牧民们表示送孩子上学涉及到一个实际的两难困境,即在保持牧业生计的同时,还要努力让孩子接受他们认为对孩子未来重要的公共教育。上面例子就显示了牧民家庭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为孩子提供教育的多种方式,这些方式往往是互相矛盾的。
四、家庭金融化
进入学校涉及到通过年度贷款和雇佣牧工在冬季照看牲畜的方式,这使得牧业生产金融化。为了筹集必要的资金将孩子送入学校,牧户使用其主要的经济资本——牲畜——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年度贷款。牧民根据其拥有的牲畜数量和种类来获得银行贷款(Marin 2008;Sneath 2012)。在巴彦洪戈尔,银行贷款申请过程要求当地区主管列出家庭的牲畜总数和种类。牧民将贷款资金用于多种用途,包括购买房产以供上学的孩子居住,以及支付教育相关费用。乌勒吉特的牧民Ganaa解释道:
“我们必须贷款。春天,我们可以依靠羊毛和其他商品的收入谋生。但到了秋天,孩子们上学了,支付学费时,我们只能用贷款。”
对于拥有较多牲畜的家庭,贷款金额可以达到1000万图格里克(2013年约合8000美元)。根据巴彦洪戈尔地方管理者的说法,如果家庭没有övöljöö(冬季牧场)的租赁权——一种私人占有牧场资源的形式——当地的银行往往不愿批准贷款。因此,贷款的获得在土地使用实践中产生连锁反应。获得冬季草场占有权使牧民更有资格获得年度银行贷款,用于支付教育费用、教育支出和维护多处住所。贷款还可用于其他开支,如购买牲畜和车辆。送孩子上学正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一位33岁的牧民解释道:
“现在,这些(两个)孩子上学了,我们没有现金去到中心购买房产并照顾那里的其他各种开支。我们可以卖一些动物,但我们不够,因此我们通过贷款来建房。然后通过卖羊绒和其他牲畜产品来还贷。”
当时这一户拥有208头混合品种牲畜,接近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数量。为了获得所需现金,牧民宁愿通过贷款抵押其牲畜,而不是通过直接出售牲畜来减少数量,因为出售牲畜会影响未来的存栏率。这一例子说明了牧民如何利用从牲畜中产生的资本,并将其投资于定居中心的房地产,这进一步加剧了分居安排的问题。
另一位较为富裕的37岁牧民,他拥有超过2,000头混合品种牲畜,且有三个孩子,分别为15岁、13岁和6岁。他们每年迁徙10至11次。孩子们上小学和中学,他购买了位于南方大约240公里的地方的房子,以便让他的长子在那里完成高中。他通过出售牲畜产品以及贷款投资房地产、交通工具和更多牲畜来筹集资金。由于孩子和大家庭成员在学年期间离开,他面临劳动力短缺,因此雇佣牧民(每月支付约100美元,约合蒙古图格里克20万)帮忙工作。一位名为Otgoo的牧民解释了另外一种替代安排,他的妻子在去年冬天第一次搬到苏木中心,当时他们的孩子开始上小学。他则独自留在牧区照看自己和其他牧户的牲畜。2013年,他每月收取500图格里克(0.25美元)每头大型牲畜(即马或牛),从照看50头大型牲畜中每月赚取25,000图格里克(13美元)。这些例子展示了教育孩子如何与牲畜和牧场的价值变化交织在一起。
贷款、雇佣牧民和新的土地使用类型直接源自牧民为了让孩子上小学而采取的措施。牧民将孩子进入学校与投资私人财产联系起来。此外,牧民提到他们因缺席冬季和春季牧场而购买土地占有权。这一证据表明,学年期间的双重居住频率可能挑战共同牧场的监护权实践,并为在缺少牧场占用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所有权和权益提供了可能性。乌勒吉特的一位年长牧民用以下的话语讨论了当代牧业情况。
“蒙古就像今天的风,没有什么是稳定的。今天,山羊皮的价格也不稳定。它曾经是2,000到3,000图格里克(1.00美元或1.50美元),但当山羊有更多羊绒时,它会上升到10,000图格里克(5美元)。就像这样……我们的国家在少数几个商人的手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致富。我们也许只有依靠羊毛和羊绒赚的钱买车。在牧区,几乎每个人都有贷款。我们为银行放牧牲畜,如果说实话的话。然后,正在上学的孩子说他们需要一些钱。公寓至少要80万图格里克(40,000美元)或60万图格里克(30,000美元)。我们没有能力买那个……然后如果我们决定在毡房区买一块地和房子,那也是20万图格里克(10,000美元)。我们去银行贷款。我们必须有保险才能贷到款。贷款利率是2%。他们以前能贷10万图格里克(5,000美元),但现在最高额度是5万图格里克(2,500美元)。我们的生活处境非常困难。人们可能会说你并不困难。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成家,我们至少需要花30万到40万图格里克(15,000到20,000美元)。”
巴特奥耶尔(Bathoyer)所说的“我们为银行放牧”,指的是为了获取资金送孩子上学,最终为孩子建立家庭的需求,明确指出了教育在金融斗争和不确定生计中的作用。
文章来源:公众号“游牧研究-CPS”,2025-04-03;转载时有删节,参考文献从略,均可前往原文查看。
原文标题:“我们为银行放牧”:牧民在教育和发展之间的新时代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