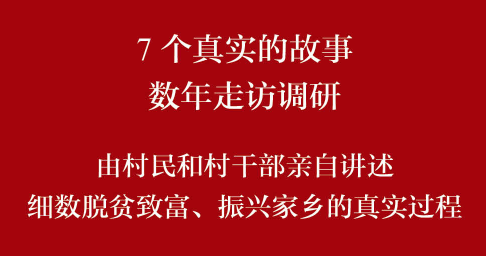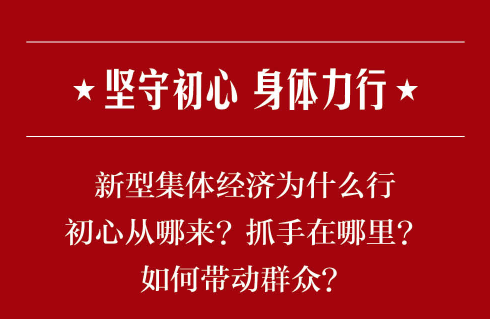黄小虎 | 上山下乡的经历是我的骄傲
来源: 醉在夕阳里 发布时间:2025-08-19 阅读:799 次
导 语
在上一期的诚食讲座中,向芯老师与听众们围绕农村生活与劳动的价值展开了深入探讨(点击此处可查看讲座回放)。这场交流不仅让大家重新审视劳动的意义,更引发了对城市中心知识观的深刻反思,当孩子们逐渐失去承担农活、参与劳动的机会,实则也同时失去了获取生活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机会。
相比之下,毛时代的中国却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片获取上述认知的沃土。对于知青黄小虎来说,伊吾军马场就是他走出课堂,投身生产一线,汲取成长养分的“改造”之地。同很多知青一样,黄小虎将上山下乡视作在生产劳动的熔炉中锤炼自我的过程。从挖水渠、修水渠时面对坚硬地面的挑战,到送粪、割草等农活的历练,再到担任代理司务长管理后勤,最后成为牧马人在草原与深山放牧,每一项劳动都成为他成长的阶梯,打破了“学生”与实际生活的隔阂,让他从“尖子生”的光环跌落,却也真切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价值,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劳动者的身份转变。
在军马场,老牧工们将骑马、放马、为母马接生、打火印等技能无条件地传授给黄小虎,使其感受到无需设防的信任与做人的尊严。这些来自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连同劳动本身带来的坚韧意志、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自然相融的体验,共同构成了他人生的珍贵记忆与精神财富。
本文冲破了公式化的“苦难连着苦难”的伤痕叙事,以鲜活的个体视角,书写了作者个人在文革岁月里的成长印记,同时,还通过处处洋溢着的劳动者的自豪感,折射出知识青年在生产劳动中汲取力量、实现自我的历程。
作者|黄小虎:曾在红旗杂志(后为求是杂志)经济部做编辑工作,1992年到国家土地管理系统任职,2008年退休以后独立从事研究工作。
责编|芒种、侯Q
后台排版|童话
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已经快60年了。近60年的人世沧桑,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也有许多事情,永远忘不了。例如,最初走上社会的情景,不论如何,只要闭上眼睛回忆,就好像历历在目。
1968年2月,我正在青海西宁市参加张大海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一天,突然接到姚佳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总后勤部所属新疆伊吾军马场到海淀区招工,同学们已替我报了名,要我赶快回京。解放军的企业,部队的职工,这对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我匆匆赶回了北京。但是我内心深处,对这次招工并不抱多大希望。事情是明摆着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母亲就被打成“走资派”,屡遭批斗,不久,父亲也因历史问题,被“揪”成“叛徒”。那时,一个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前景是暗淡无光的。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去见了马场来京招工的万天恩同志。轮到谈我的情况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讲了一大堆好话,我自己却只是极简单地表了一个态:我愿意到军马场去接受锻炼,如果能去,一定努力工作;但如果我的家庭情况不符合马场的招工条件,我也能充分理解并正确对待。不知是大家的好话起了作用,还是我的“正确对待”感动了老万,几天后接到通知,我被录用了。那时的感觉,真好像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父亲也很高兴,说:“不管怎么样,也就是参军了。年轻人应当离家远一点,去见世面。”
马场共招收了108个北京知青(其中有27个是人大附中同学)。3月12日,我们从北京站坐火车经西安到哈密,改乘卡车翻东天山,到达坐落在巴里坤草原上的伊吾军马场,已是18日了。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四连,因我们的到来,四连一度被称为“红卫队”。
哈密北边的东天山又有南山、北山之分。巴里坤草原夹在南、北山之间,面积近3000万亩,海拔1600米至1800米,是新疆第二大草原。伊吾军马场占据的则是草原东部最大、最好的一片草场。草原中部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柳条河,由南山和北山的雪水融汇而成。说是河,其实水很浅。马场的各农牧连队的马群,有的夏牧场在北山,有的夏牧场进南山。冬天,大多数马群吃完草后,都要到柳条河饮水。所有农牧连队都有大片农田,主要种植燕麦,由于无霜期短,不能收获籽种,种植的目的是秋天割麦草,用于冬天给马群补饲。
四连即红卫队在柳条河北边,我们入驻后接受准军事化管理,早晨列队出操,上午下午分班排劳动,收工后集体学习、分散娱乐,晚上统一熄灯睡觉。当时马场正处在扩张期,多养马就要多种草,多种草就要扩大水利设施,我们红卫队所干的活儿主要是挖水渠、修水渠。马场的农田都是机械耕作的大条田,灌溉系统是横平竖直的干渠、斗渠、支渠,干渠和斗渠由解放军286部队负责施工,我们则主要承担支渠的挖掘任务。那时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地面坚硬得一镐头一个白点,对我们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我们挖成土渠以后,还要铺设水泥板,就主要由有专业技能的老职工去做了。
分配给知青的还有一个活儿:送粪。冬天连队积攒了不少马粪、牛粪、人粪,春种前把这些粪装上大车,卸到地头,再撒到田里。红卫队基本上独立劳动,与老职工接触不多。这样干了几个月,场里决定解散红卫队,把北京知青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我和另外十几个人被分配到三连。
三连在柳条河南边不到10公里的样子,再往南约5公里就是哈巴公路了。我们到三连以后还是先分配到农业班,干的活儿就多了。如起圈,把马圈、牛圈、羊圈里积攒的厚厚粪便挖出来、清干净,堆起来沤肥,有时还要掏旱厕所里的人粪;如跟车,跟着车把式赶的胶皮轱辘大车,搬、运、卸跑运输;如收获燕麦草,首先是割草,使用的工具是新疆特有的扇镰,长木把的底部装一只半米长的大镰刀,人站立着贴着草根挥舞镰刀,一片燕麦草应声倒地。干这个活儿需要力气,也要摸索技巧,但还是难免腰酸腿疼,搞不好还可能伤到自己。其次是装车,将散落的燕麦草归拢成大堆,马车或汽车过来,我们用长把铁叉或木叉铲草装车,车上有人接应将草铺平,越铺越高,最后要将叉子举过头顶,才能把草送上去。有的老职工一叉子下去,能叉几十斤草,既有力气也有技术,我们慢慢也有提高。如此这般,很快就到年底了,北京知青纷纷申请到马群去放马。
好几个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马群,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我能不能去,领导始终不松口。大约11月间,连指导员黄长丰找我,这是个50年代入疆的老兵,老成持重、待人严谨。他说经研究,决定让我做连里的代理司务长。我虽不情愿,也只能服从组织决定。连队职工100多人,加上家属小二百人的吃喝日用,司务长都要管;连队食堂的柴米油盐酱醋菜肉,更是不能不管;还有各个马群的后勤供应,也是必须管。
我先从改善食堂饭菜入手,制定的食谱包子、饺子、面条、炒菜、炒肉、炖菜、炖肉,每天不重样,大家高兴。我还骑马到北部的6连去赶了2只毛驴回来,拉石磨碾黄豆点卤水豆腐,既给食堂增加菜品,也卖给家家户户。后来一只毛驴半夜被狼吃了,但基本没有影响豆腐供应。连里还派人帮助挖了一个大菜窖,我从哈密采购了很多白菜、圆白菜、土豆、胡萝卜、皮牙子(洋葱)等,存到窖里供应食堂、马群和职工家庭。我经常赶着一辆马拉或牛拉的小炮车,给各个马群送米面肉菜等生活物资。总之我工作努力,连里上上下下也都满意。
司务长配有坐骑,我虽没能放马,也可以骑着马到处跑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去马群工作,便尽可能参加与放马有关的事情。马驹子长到约一岁,要在屁股上打火印,就好像身份证一样,为的是方便人辨识。打火印是个危险的工作,牧工把一群马驹子赶入马圈,人要在马跑过身边的瞬间抓住马的右耳和掰住马嘴,把马头向左上方掰扭,让马失去重心摔倒在地,人压在马身上,有时要二、三个人才能压住,负责打火印的拿着烧得通红的烙铁,在马的左屁股上使劲按住,冒出滋滋响的白烟,闻到焦煳的味道,大家才放手让马跑去。我有一次没抓住马耳朵,马飞起后腿踢到我脑门子,晕晕乎乎了好几天,眼镜也碎了。还有,为了防止传染疾病而给马群打针。建一个狭窄的、长长的木栅栏通道,把马群赶进去排队,人站在栅栏外边给马屁股打针。这个活儿没有危险,但也很费周折。
我当司务长一段时间,指导员黄长丰和连长都调走了。当时马场扩大规模,把西边相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划过来,几乎整个巴里坤草原都属于马场了。过去连队直属场部,扩张后变为连——大队——场部三级设置,黄长丰等各连队的主要干部,都调到新组建的大队担任领导了。新任三连指导员郭传经是个大学生,与北京知青相处融洽,我多次向他申请去马群放马,他最终同意。
大约1969年11月,连里分配我到十群放马,但交接司务长工作要查账,查出我的账目亏损2400元,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的主观原因,一是菜窖没有经常通风,大白菜烂了800元,二是卖米面油和菜等足斤足两,不计损耗,三是食堂饭菜定价偏低。客观原因,连里会计因受政治审查被停职,在一年时间里没有会计监督我的账目。组织上很宽容,没有追究、处分我,决定把亏损额按挂账处理。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我回马场探望时得知,这笔亏损一直挂在三连的账上。交了司务长工作,我到十群报到,如愿以偿成了一个牧马人。
马场的马群分两种,大马群和驹子群。大马群又叫儿马群,儿马即公马,强悍的能占有十几匹母马,弱一点的也能有七、八匹,自然形成一个个小群。一个大马群可以有十几个这样的儿马群,大约一百几十匹母马。这些母马一年一胎生育小马,小马三个月大就要与母马分开,送到驹子群饲养,长到约一岁打火印,大约二、三岁左右就可以向部队输送军马了。70年代的解放军已经没有骑兵部队了,但大量运输任务如炮兵驮炮、后勤运送物资等,仍然需要马匹。80、90年代以后,部队建设越来越现代化,不再需要军马了,军马场因此萧条、落败,这是后话。当时的马场对各连队的母马群统一编号,三连的是九、十、十一、十二四个群,还有一个不编号的驹子群。大约于1969年初,连里抽调了一些北京女生,到驹子群放马。女孩子放马,一时间成了轰动的新闻。大约1969年5月,场里决定在二连组建一个女子放牧班,把三连的郭义和闫红歌调过去了。
十群的定居点在南山坡上,有一个很大的马圈和儲存燕麦草的棚子,还有一间很大的土坯房,除了夏天的6、7月和8月上旬进山里放牧,其余时间我们都住在这间房里,轮流值班看护马群。巴里坤草原9月入冬、5月入春,一年里多数时间都是白雪皑皑。牧工的标准装备:一件盖过脚面的老羊皮大衣、一条老羊皮裤和一双长筒毡靴,我们每天棉衣棉裤外面,还要穿上这几十斤重的装备,才能到冰天雪地里放马。
巴里坤马是蒙古马的一种,积雪再厚也能刨开雪吃下面的干草。因此整个白天和晚上前半夜,都让马群散布在南山坡自己找草吃,半夜将马群赶回圈里,补饲少量玉米、豌豆、高粱米和较大量的燕麦草。马群吃饱后赶出圈外,它们就会一溜小跑,奔向柳条河去喝水,喝完水再将它们赶回南山坡的圈里休息几个小时,天就快亮了。这样日复一日,群里的几个牧工分班轮流,一刻不停都有人守候在旁,观察马群是否有异常情况,如是否有病马,是否有母马快要生产等等。发现病马要及时把它赶回圈里,通知兽医来治疗。冬天是马群产驹的高峰期,对待产的母马要贴近查看,一旦临产必须在旁看护,直到马驹站起来吃上母奶。对那些站不起来的小驹子,要帮助撕去胎衣,手扶它站起来,否则马驹就会冻死。个别十分弱小的驹子,还要设法避开母马的攻击,把它抱到屋里取暖。
正常情况下,马群分散在坡上吃草,值班的人可以找个背风的坡,在齐腰深的雪里挖个洞,半躺在洞里躲避严寒。但如果有异常动静,就要立刻翻身上马去应对。譬如马群突然受惊四散奔跑,你就要快马跟上,逐渐稳定它们并清点数量,如发现有跑散的儿马群,还要四处寻找赶它们回来。冬天的草原经常有暴风雪,狂风卷起雪花排山倒海般吹来,搅得昏天黑地、不辨方向,柔软的雪花変得像刀子一样,打在脸上疼痛难忍。遇到这种情况,马群往往随风狂奔,我们也必须放马跟上,直到马群在风小的地方停下,再慢慢辨识回家的路。
冰雪无情但也能给人带来快乐,每当雪后初晴,不值班的牧工就会骑马到雪原上,循新鲜足迹寻找觅食的狐狸或野兔。新雪又厚又软,狐狸和兔子跑不快,骑马追上俯身用马鞭抽打,可以收获狐皮和兔肉,其乐无穷。我曾写过一首诗《大雪夜牧》,记述当年的生活:
龙争虎斗苍穹暗,败甲残麟落满天。
还我天山真面目,万里冰封朔草原。
狂风乱作如针刺,人睏和衣卧雪渊。
会当飞猎狐和兔,百里奔袭入梦甜。
夏天进山放牧,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大马圈沟和小马圈沟是三连的夏牧场,十群和十一群的放牧区是大马圈沟。离沟口很远就听到涧水的轰鸣声,穿过一片从山上延伸下来的松林,就是宽阔的、布满大大小小石块的河道,其中不乏巨石,可见这里曾经有过大水。现在的水不能算大,但流速很急、声音很响,由于这里比较宽阔,就成为我们赶马群来饮水的地方。沿着涧水右岸上行,到了一东一西两座山镇守的沟口,东边的山笔直陡峭,骑马也不便行走,西边的山则有缓坡和台地,便于放牧。在靠近涧水边坡的台地上,建有一个石头垒砌的小屋,分配给十群使用,但只能容几个人栖身,其他人还要搭帐篷居住,十一群则全群牧工都住帐篷。石头房子外面搭了一个炉灶,两个群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抬眼望去,身边的两座山高大巍峨,从上到下长满了松树,青翠碧绿、生机盎然。远处则是山外有山、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最高的地方还隐约可见皑皑雪峰,那里的海拔已在4000米以上。
我们在山里依然日夜轮流值班看护马群。由于东边坡陡林密草疏,所以尽可能让马群在西边山上活动,但也总是有个别儿马群悄悄跑下山涧,钻到对面树林里去,我们也只好钻进去寻找,免不了被树的枝杈划破衣服甚至皮肤。西边山松林的间距大,林子里的草生长茂盛,还有山梁和台地,适合马群分散进食。树林的上面又有高山草甸,马群穿出树林就可能越爬越高,为了防止危险,我们下马端坐在高处,不让马群上来。山里的温度低,白天还是要穿棉衣棉裤,晚上也至少裹一件棉大衣。“山里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一次我早上值班时天气晴好,突然一阵狂风和雷鸣闪电,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棉衣、棉裤淋了个透湿,过一会儿雨停了又是晴空万里,大约中午时分,棉衣棉裤又都晒干了,着实感受了天山的神奇。
在山里放马,经常遇到或看见马鹿、山羊、大头羊、野猪等动物。群里配备有一支三八式步枪及几颗子弹,目的是防身但偶尔也会用来打猎。记得有一次十一群打了一只野猪,分给我们一些肉,我们到草原上采摘新鲜蘑菇来炒肉,非常美味。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极其深刻,终身难忘。听老牧工说,东边山上有一道梁可以通到小马圈沟,于是我在一个不值班的日子骑马上山,到达草甸子的高度后,向东穿过山涧到对面山上,寻找了好一会儿,才在下方找到了一条东西向的山梁。山梁的入口很小,不易被发现,山梁的下边和上边都是松林,因此在远处特别是下面,根本看不到这里有条梁子。进入梁子我惊呆了,梁上开满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鲜花,而且花朵出奇的大,我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野花。没膝的野草青翠欲滴,簇拥着上面的花朵争奇斗艳。花朵们随风舞动,仿佛在向我点头致意:“欢迎来到花的世界”。看着梁上梁下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环抱着这一片花海,我当时的感觉是此景只应天上有,这就是所谓天堂吧!我小心翼翼地驱马前行,生怕踩坏脚下五颜六色的花毯。在山梁上盘桓了一个小时,终于下到了小马圈沟,到达十二群的驻地。这样的自然美景可遇而不可求,我一辈子只遇见过这一次。但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过大自然洗礼、熏陶的人,对任何人造的雕饰,恐怕都提不起兴趣。
当年我曾写过一首诗,反映南山的牧马生活:
云内青山云外峰,马踏深山不见踪。
树郁峥嵘漫天际,石怪嶙峋卧绿丛。
数见雷鸣惊落雨,履闻涧舞跃长空。
却问牧人向何去,笑指苍山几千重。
以上所谈,是我在马场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那么我的政治、思想、心路历程又如何呢?1998年是我们到马场30年,有悔还是无悔,是知青们的争论话题,后来知道了但不想参与争论。人的成长道路千差万别,不能要求有统一的认识。倏忽又将近30年过去,我基本坚持当年的认识,但也有的问题需要完善。
下面的文字,是在1998年文章基础上,做了少量修改。
马场虽然地处偏远,但并不是世外桃源。每次,只要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点政治动静,这里就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阶级斗争的风浪”。阶级斗争,有斗争对象,有依靠对象,有团结对象。我的父母有“严重问题“,显然是不能依靠的;但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没有复杂的历史问题,又是在学校入的党,因此可以归于“可教育好子女”之列,算是个团结对象。
那个时代,所谓团结对象,亦即不可信任分子,要随时注意他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基干民兵,我不能当;选先进、评“五好”之类,即使群众一致同意,领导也不敢批准;党员予备期,五年、六年、七年,仍不能转正;清理阶级队伍,我一度被列入另册。我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过集体生活,受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作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前,我长期是学校里的“尖子”,担任班、团干部,可谓“一帆风顺”,自己也常常有志得意满之感。可是,一场暴风骤雨之后,我突然从颠峰跌落谷底,从天上掉到地上。过去,我是自己所热爱的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却成了队伍里的嫌疑分子。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来说,如此巨大的反差,带来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创痛。
那些年,每当我读到唐朝诗人王驾的诗句:“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总是联系自己的遭际,感慨不已。
应当特别说明,我的遭遇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决定的,并不是马场的领导和党组织对我有什么偏见,相反他们是宽容和大度的。我出身不好,政治上不符合当时基干民兵和先进模范的标准,但让我代理司务长,以挂账的方式处理我的亏损,委婉传递的信息却都是信任。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任务,有自上而下的要求,处于边境地区的马场必须按上边要求拟订名单,我也必然榜上有名,但最终并没有清理我 ,显然是有马场的最高领导拍板决定。
马场的最高领导是政委冒月鸿,我到十群后一次听美国之音广播,被人告发收听敌台,冒政委在全场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听说后要求与他面谈,向他陈述马场信息闭塞,听美国之音是为了多了解世界局势,并不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表示理解,但也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听了,没有任何颐指气使、装腔作势。他还仔细询问我读了哪些书,并谈了他对一些书(如《红楼梦》)的看法,向我推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劝我多读毛主席著作等等。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始终和颜悦色给人以温暖。当年,一个“收听敌台”是可以给人定罪的,但冒政委却不动声色把事情压住了。
我后来听说,他原是某上层军事机关的现役干部,因得罪人而被整肃,下放到非现役的基层,不知确否。我想可能是有这样的经历,他才感同身受,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十分慎重。1972年我调离马场前,场党委批准了我的党员预备期转正问题,说明马场组织和领导,对人是高度负责任的。
还应当说明,尽管个人遭受不幸,我对主导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路线并未有丝毫怀疑。相反,我完全接受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来观察社会,观察别人。一方面,我是当时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又是这一路线和理论的捍卫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必然要在思想上寻找平衡点。我阅读历史,发现举凡大的社会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群众起来,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无辜的牺牲者。我想,“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做出牺牲,我应当毫无怨言。只要春色尚在,在不在我家,倒无关紧要。就这样,我找到了支撑自己的平衡点。
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扭曲的心态,仍会感到阵阵苦涩。但是,我也始终不愿彻底否定那心态。毕竟,甘愿牺牲的出发点是纯洁的,丝毫没有现在社会上到处弥漫的金权的臭味。
现在的许多书籍、文章,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遭遇,往往是苦难连着苦难。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据我的体会,世界上最卑贱、最微不足道的人,生活中也有欢乐。劳动的欢乐,与朋友交往的欢乐,获取知识的欢乐,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欢乐,这都是天赋的、苦难命运也剥夺不去的人权。
伊吾军马场,是我告别学校生活、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以前,也有机会接触工农,但身份还是学生。这次,则是投身社会底层,成为普通百姓的一员。至此,我才真正了解工农大众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才真正深入到他们的感情世界。那些朝夕相处的老牧工们,王发财、张厚世、程宏毅、杨宏根、程爱、庞国禄、安登玉……,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劳动的技能。骑马、放马、压马、套马、相马、驯马、观察病马、为母马接生、打火印、分群、检疫……。
每当向部队输送一批军马,每当听到或看到马群风驰电掣般地从身边跑过,我就会觉得自己与老工人一样,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心中油然升起劳动者的自豪感。那些老工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出奉献,自己从社会得到的却是极其有限。他们对生活没有很高的追求,因而很容易满足,总是充满快乐。他们也有缺点,有时狡猾、自私、斗小心眼,即使这样时,依然透着朴实。他们有自己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从不受上层社会政治风云变化的影响。只要你正直、诚实、能吃苦,他们就信任你、看重你。和他们在一起,不用担心背后会射来冷箭,能体会到做人的尊严与乐趣。
离开马场以后,我教书,做编辑,做理论研究,一晃50多年了。回想起来,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最脚踏实地的一段时光。5年间,我仿佛从泥土中汲取力量,之后,才能在人生阶梯上艰难登攀。
从北京一起到军马场的青年学生共108人,后来又来了几百乌鲁木齐学生。此外,还有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那时,大家都正年少,充满朝气和热情。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我与不少人结下深厚的感情。有的人,过去虽然相识,但真正相知,却是在马场。这些人中,不少和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变故,历经种种坎坷和挫折。但是,大家都尽力超然“物外”,彼此很少诉说个人的不幸。朋友相聚谈论的,是世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马场的事情;交流的,是读书的心得和走上社会后的人生体验。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从友谊中汲取力量,获得慰藉和快乐。那时,大家都是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的亲人,这种友情更显得格外珍贵。犹记得,几乎每逢休息,我都不惜骑行几十里,与朋友聚会。偶尔不出门,也一边作内务,一边盼望有人来访。
离开马场以后,或因山河阻隔,接触无多;或因经历不同,共同语言渐少;或因工作缠身、生活担子重,无暇顾及,渐渐与过去的朋友疏远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人生聚散本无常吧。但是,无论怎样,那段人生旅途中结下的友谊,永远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因“家庭问题”而影响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是不公正的。但就个人的成长来说,这也未必全是一件坏事。毛泽东说过,地位的变迁,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他还曾引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据个人的体会,人经变故跌入社会底层,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能比较冷静、客观、深入地观察社会。记得是在“评法批儒”之潮中,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昏吃蒙睡又一天,不知今夕是何年。据云国中多建树,革命新贵尽开颜。老将却道不如昔,牢骚怨言飞满天。我亦不知谁正确,闲来无事听唱片。”诗中的情调是冷峻、迷茫的。并透出内心深处对“四人帮”一伙的不满和嘲讽。这种冷眼看世界的态度,是由当时我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有了这段经历,我对毛主席经常说的“卑贱者最聪明”,才有了真切实在的体会。
地位变化,失去权势依靠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促使人发愤自强。我的朋友杨镰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无从悬想身后事,不应遗恨少年时,”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虽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奋发向上的情怀。不留遗恨的具体表现,除了努力作好本职工作,就是刻苦学习,认真读书,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丰富自己的人生。
我自知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生大概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因此下决心自学打好文化基础。回想起当时读书的情景,真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不管是经典著作,还是教科书、工具书、普及读物;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理论,还是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戏剧、回忆录;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能找到的书,就要设法搞来读。每天,除了工作或会朋友,就是读书。特别是每当夜深人静,在煤油灯下一边读书,一边凝神思考,细细品味所读的内容,真是其乐无穷。
我读书,有两个习惯,一是作笔记,将要点抄录下来,有的甚至全部抄录。例如,从杨镰处借得《古诗源》,原原本本,我夜以继日用半个月时间全部抄录。完工的时候,觉得全身精力都要耗尽了。一是写心得,有的是读一本写一篇,有的则是读一段写一点。我读《红楼梦》,就是读一、二章,写一篇体会,二三个月下来,集成一本。我读书的速度比较慢,但快与慢是相对的,积慢可以成快。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我没有大学学历,但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却被红旗杂志选中作经济理论宣传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得益于马场5年间(还有后来大同一中5年),自学打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那5年是我一生中精神生活最充实的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收获。高尔基把社会当成大学,对我来说,伊吾军马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
马场座落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上,这里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处处银装素裹。我们穿着数十斤重的老羊皮大衣,老羊皮裤和毡筒,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在没膝的积雪中放牧,追狐狸,打野兔。此时,即使是文弱书生,也会凭添几分粗犷豪放。夏天,随马群进山,则眼观青山、碧水、绿树、蓝天、白云,耳听松涛似海啸,涧水如雷鸣。每有晴雨,草坡上到处有硕大鲜美的草蘑破土而如;时逢春初夏末,美丽的山花遍布山野。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纵然是彪悍之士,也难免生出似水柔情。巴里坤草原辽阔无垠,人烟稀少,没有城市的喧闹,文化生活也比较单调,但是我们却能尽情欣赏大自然的壮丽,体会她变幻无穷的韵律。
拜伦的诗曾经描述:人置身于自然之中,坐在山岩,对着河水,觅入树林,走进那从没脚步踏过的地方,和人的领域以外的万物共同生活,这不算孤独,这不过是和自然的姣丽展开会谈,打开她的富藏浏览。然而,如果是在人群、喧嚣和杂沓中,成了一个疲倦的游民,茫然随世沉浮,周围尽是阿谀、追随、钻营和求告,到处是不可以共忧的、荣华的奴仆,没有人祝福我们,也没有谁可以祝福,这才是举目无亲,这才是孤独。
对拜伦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我是到马场以后才深切体会到的。
马场5年,我们终日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陶冶性情、净化灵魂、实现自我。后来,我又返回城市,却常常感到茫然若失。人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得到的,却是自己最不想要的。几十年了,每当我在尘世的喧闹中感到孤独,就会怀念起当年的“烟霞闲骨胳,泉石野生涯”。
“文化大革命”后,常常可以听到“被耽误的一代”的说法,我认为,确有一些人如理工科天赋较高的人被耽误了,但用它来概括一代人是不全面的。在那动乱年代的风云变幻之中,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磨难,失去了许多本可以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在逆境中,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一帆风顺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当年,保尔·柯察金审视自己青春的苦难经历,得出“我所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结论。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恰当的。
每一代人都有成为自己骄傲的独特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就是在上山下乡之中经受磨难、积蓄力量,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重要的开拓和推动作用。
文章来源:公众号“醉在夕阳里”,2025-06-28
原文标题:人生之路 | 黄小虎:我的伊吾军马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