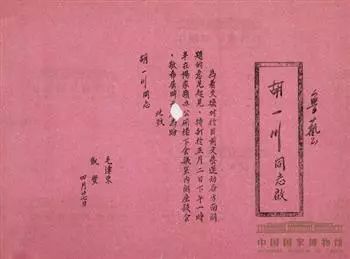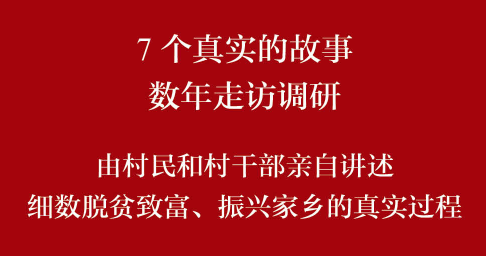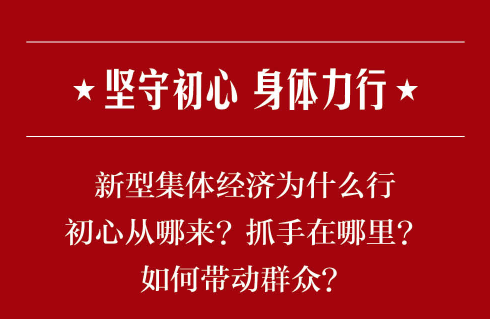曹征路 | 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四十
来源: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发布时间:2020-12-09 阅读:3180 次
导语
在文艺界,围绕着延安整风运动的争议一直不断,本篇以丁玲、王实味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呈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一些基本事实。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文艺界整风展开的背景和目的,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丁玲与王实味并没有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产生矛盾,他们反而是那个时代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当时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凝聚起力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第一位的。
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四十)
延安整风运动中影响最大最长久的事情,莫过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了。
这倒不是文艺界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而是因为文艺界名人多、回忆多,近年来的争议也最大。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重镇,所以颇具典型性。
本篇以被人们反复提起的丁玲、王实味为例,分析座谈会前后的一些基本事实。
还是先引一段某作家的关于知识分子悲剧的结论: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灌输’的消解剂,之所以是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消解剂,归根究底,无非两个原因,一是知识分子对此岸吞噬彼岸的抵制,一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彼岸意义的虚拟性的无意识破译。进而言之,在世俗性宗教不发达的中国,知识分子天然地构成真实彼岸的主体力量,因而天然地具有反抗此岸扩张、排拒虚拟彼岸的禀性。这样,此岸向彼岸扩张的欲望愈强烈,政治的彼岸意义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强烈,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愈恐惧,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愈深刻。知识分子必然要被当作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简而言之,灵与物的冲突,彼岸与此岸的冲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冲突的本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则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开端。
某作家使用的基督教概念此岸彼岸,用来替代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天然矛盾,意思是艺术家追求彼岸,要暴露政治家的黑暗,所以被整肃。他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对此次集体抗议运动的直接回应。讲话不单是否定了知识分子所特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而且完全排除了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彼岸在现代社会独立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就是由一批知识分子传播马列主义开始的。早年共产党的组织以及它的领导层也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在各个历史时期注重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在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延安,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是他们的自主选择。
汪精卫公开投敌后,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针对有人污蔑延安愤怒地说: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共产党欢迎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理所当然希望知识分子对革命做出贡献,而不是要知识分子来改变革命方向的。理所当然希望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不是为表现个人的。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工农为基本力量的革命党,从来也没有隐瞒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最高纲领。至于有思想争论,有路线斗争,在党内高层都是要经常发生的事,在文艺界就不可以有吗?
某作家对这些历史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夸大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矛盾,意在说明知识分子与马列主义天然对立,重弹“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老调。他在文中列举的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罗峰等人只是文艺界的一部分,不代表知识分子全体。何况他们本身就是共产党员,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他们也不是什么“暴露派”,向往新生活、追求革命理想是他们作品的主基调。
在延安整风中安排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并不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央正式决定召开的。据文献记载,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明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当年延安的文化人,尤其是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作家、评论家,在供给制环境下,由于伙食单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艺成就与文艺观念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形成不同的山头。当时俗称:“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
萧军
1941年7月8日,“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约见谈话,反映一些文艺界的情况。7月18日,萧军应约到杨家岭与毛泽东谈话。谈话持续7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方方面面,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初次谈话,萧军对毛泽东很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在与萧军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感觉问题的严重性。其后,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经受邀到毛泽东驻地谈情况,主要有刘白羽、李伯钊、丁玲、艾青、萧三、罗烽、舒群、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还给许多作家、文艺家写信了解情况,同时还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如同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
毛泽东掌握的情况越多,越觉得有必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好好地谈谈,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据胡乔木回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
一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
二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问题;
三是思想倾向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
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问题;
五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情绪问题。
当时毛泽东对文艺家的尊重,可能今天一个县委书记都做不到。就像诗人公木回忆的那样,开会不是简单发个通知,而是发了正式的请帖。延安物质匮乏,纸张奇缺。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延安文艺座谈会请帖”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的,算是延安当时最豪华的印刷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帖
前两次会议是自由发言,焦点人物是萧军,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对整风提出批评,遭到另一些人的反批评。还有人大讲文学基本知识,主张用文学教程规划党的文艺政策。5月23日,第三次会议在临近下午讨论结尾时,朱德发了言。他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和一些同志的观点,然后现身说法,认为一个人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
他动情地说:“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朱老总讲得很激动,“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个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朱德用浅显通俗的大白话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点明了会议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文艺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整个座谈会的讨论到朱德讲话为止。
晚饭前,全体到会人员集合,由摄影师吴印咸为大家照合影照。拍照没有专门排座次,大家入座后,毛泽东面朝大家站着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总身边,这才放心地坐下,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对嘛,照相坐前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晚上由于来听讲的人增多,会议移到院子里,临时支起一盏煤气灯,由毛泽东作总结讲话。
这就是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提到的《三八节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直被学术界当作文化人与当年延安主流政治发生激烈冲突的标志性作品,几十年来争议不断。那么当时情况真的像一些研究者说的那么严重吗?从毛泽东的轻松的口气看,他并没有把《三八节有感》看作很大的一件事,无非是说你跟男同志平起平坐了,明年就不要发牢骚了。
从《三八节有感》的内容看,无非是表达了她对延安妇女生存状况的不满,被一些批评者戴上了“个人主义”和“挑战权威”的桂冠后,在整风运动中受到点名批评,更使这篇杂文传到了国统区。后来更被说成是“集中表现了女性认同与阶级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对抗”,而成为女权主义批评家眼中的经典。美国学者白露认为,
丁玲在她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中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性爱、觉悟和社会。她问道:是谁掌管性表达和传宗接代的大权?是妇女们自己还是婚姻主管机构?既然性别决定了她们在觉悟上与他人不同,那么这一点在延安能不能得到肯定?最后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怎样才能争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不明了这一女权主义的性质与广度,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由《三八节有感》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争论。
可是丁玲本人对女权主义并不赞成,更不认为妇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矛盾。许多知识女性包括陈学昭、韦君宜这样一些高学历者,在那个年代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就在于延安的革命氛围,让她们看到了一个妇女彻底解放的乌托邦。丁玲为女同胞开出的药方也是要“忘记自己”,“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丁玲
其实早在1928年冬天,因为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大红大紫的丁玲就受到《真善美》杂志“著名女作家”栏目的约稿,“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长短,稿酬从优,而且可以预支”。丁玲谢绝了这一邀请,当编辑一再坚持的时候,丁玲直截了当说:“我卖稿子,但不卖‘女’字。”
丁玲的女儿后来看到《三八节有感》也很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会引起风波,她回答说:
就是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了‘土包子’老婆另找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
可就这么点事,厄运却伴随了她一生。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当初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掌了权就要施威,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比旧军阀文明。
1958年,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著名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重提丁玲《“三八节”有感》以及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期间她被打成右派。
到了1980年代,这一切又被翻转过来,这些作品成了启蒙主义的样板,“一个感伤主义者的内心认知”,是“五四文学观的再现”。这种重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老调的文学批评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曾经供职于美国中情局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
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无法遮蔽她对延安共产政权的不满,而短暂的回到了她过去的颓废、虚无主义的情绪。
于是掌权的批评家也跟着夏志清摇旗呐喊。但在其后,丁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丑化共产主义,反而用一系列言行证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人。于是丁玲又被当成了左派,遭到周扬为代表的权势者打击排斥丑化。
面对历史的吊诡,丁玲表现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
当初把我打成右派的人,就是今天把我打成左派的人。
周扬
当年,鲁迅在论证左翼很容易变成右翼时说: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
读懂了鲁迅,便读懂了丁玲的赤诚。
其实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并不在意是左还是右,他们在意的始终是自己的荣誉地位。他们把参加革命当作投资,革命成功后他们就要求分红,左派上台他们比谁都左,右派上台他们比谁都右。共产党内的这种状况自然给某些势力以可趁之机。
王实味
与丁玲《“三八节”有感》遭遇相同的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文章而言,《野百合花》集中表达了王实味对延安在和平条件下公共权力异化的敏感,以及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焦虑。与丁玲一样,王实味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提供一剂苦口的良药,驱除现实中的缺陷,“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但杂文用词尖刻,“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为五等”等等,使延安的老干部看了很不适应。
《野百合花》的一部分章节,除了在《解放日报》发表,还贴在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来看的人很多,甚至还惊动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曾经在深夜提着马灯来看《矢与的》壁报上王实味的文章。当王震一行应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之约,来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看完王震就大声骂起来:
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指王实味)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骂了之后,王震又来到《解放日报》社,找博古责问。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王震与贺龙一起狠批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这个事本来属于思想斗争范畴,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不像丁玲很快做了检讨,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结果使斗争逐步升级。
那时共产党对解决思想问题还没有经验,往往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实际上王实味1937年到延安,被安排在鲁艺教书,后来又调到马列学院(后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这期间,王实味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并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贡献巨大。也正是因为贡献大,他在供给制体系中地位突出,当时他的津贴四块半,与边区主席林伯渠一样,仅比毛泽东少五毛钱。也许正是他的傲气和待遇,激怒了周围的许多人,把他的问题上升到反党的高度。
1942年6月13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丁玲作了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在发言中,丁玲承担了发表《野百合花》的全部责任,她说:
《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
实际上当时舒群已正式继任主编并身在报社,丁玲已不再是主编,但她还是把责任揽下来,意在解脱其他人。但王实味还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坚持不改。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由中宣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0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到了年底,王实味被关押起来。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陕北实施重点进攻。王实味也随中央机关撤离出延安,他所在的看守所遭到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示对王实味应如何处理。中央社会部批准就地将王实味秘密处死。
很多材料显示,毛泽东直到1949年才得知王实味的死讯,毛泽东闻讯发火,对当时签署秘密处死王实味的负责人康生怒吼,“你还我一个王实味!”
康生
王实味当然不是托派,后来公安部正式为他平了反。但“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王实味是标准的左翼文艺青年,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他不可能没读过。我们今天回顾这段沉痛往事的时候,当我们仔细琢磨丁玲为王实味承担责任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二人在精神上与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相通。
在当时的延安,像王实味这样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极为罕见。与那些有留苏背景的海归人士相比,王实味才真正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比王明那种人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分裂更敏感。王实味对边区官僚主义现象的批评,可以联想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念和“异化”理论,却最终被说成“小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0年代以后为他鸣冤叫屈的人,是理解不了王实味的,他们把王实味奉为自由化的鼻祖。其实王实味才是“真左派”,与丁玲一样,是那个时代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那里,不是他们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有矛盾,而恰恰是认为延安不够社会主义不够马克思。
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七大时总结与王实味的斗争:
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毛泽东对一介书生的批评如此高估,恰恰是因为他在王实味的批评中看到了“不断革命论”。反过来说,如果仅仅是小资产阶级,仅仅是个人主义,毛泽东完全没必要承认“吃了败仗”。因为个人主义早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声名狼藉,根本不可能与集体主义抗衡。
细究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大的个人主义精神的失落。第一次是五四以后,个人没有出路,经历了一次寻找“集体”的痛苦;第二次是反右以后,个人更无出路,经历了一次“国家”认同的痛苦;第三次就是1990年以后,个人欲望得到部分满足,“身份质疑”成为时尚,经历了一次“拜金拜权”的痛苦。
让毛泽东难于释怀的,恰恰在于王实味的理论挑战性。王实味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达了他的焦虑,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的焦虑。
1941年8月2日,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就激烈地指出:“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王实味批评的这种现象无法消除。在延安供给制干部待遇差别不大的条件下难以消除,即使是到了夺取政权以后也无法根除。一方面供给制提高了效率,是革命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供给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主义。
毕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阶段论”必须实行,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到来。
通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延安暂时解决了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并凝聚起创造新中国的力量。
但王实味和丁玲带给延安政治生活的冲击,革命理想与官僚主义的冲突却没有完结,以工具理性为特点的官僚体制与共产主义信念之间的冲突没有完结。
这一事件开启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的先河,带来的伤害也是深刻而久远的。共产党如何在公共领域建立起崭新的现代性,“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