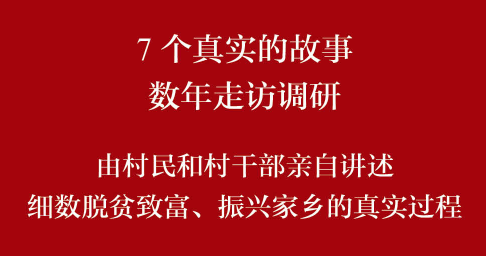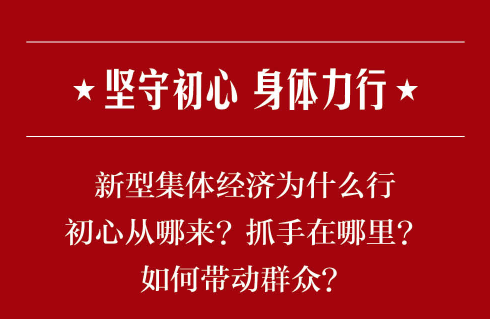《曹征路:重访革命史》读后感 | 革命、理性及其它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20-10-12 阅读:3284 次
导语
从2020年9月9日开始,我们连续刊载《曹征路:重访革命史》的系列文章,同时倡议读者朋友们和我们一起阅读打卡,分享感想,以实际行动纪念毛爷爷!
今天的文章就是我们一位读者朋友关于其中三篇的感想,这三篇分别是第十篇:古田会议决议永放光芒、第十一篇:毛泽东的现代性代表了历史进步最本质最前瞻的要求、第十二篇: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期待大家在系列连载的文末留言,分享您的体会!
曹老师第十篇,关于古田会议。其意义并不是简简单单开了个会,而是经历了之前诸多经验、教训、分歧、斗争……之后建党建军原则的总结。曹老师前面写得很细,用了五个篇章的篇幅,为的就是说明这一篇古田会议的水到渠成。
现实中并没有理想的、符合教科书标准的无产阶级,毛主席他们的做法则是积极召唤、改造出不断趋向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这的确是至今值得重视和借鉴的。
我自己在阅读此篇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也是参加过古田会议的人回忆当年毛党代表如何做思想工作:
不断深入到各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
真是“教员”本色。
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通过思想改造不断清除小生产者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可能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批评者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唯意志论”;肯定者称之为“发掘革命潜力”、“促成人的觉醒”;中立的研究者称之为“话语先行”、“思想领先”、“革命话语乃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构成性因素。”
我的想法则是:毛教员强调的政治挂帅、思想改造,其实并不是悬空的理论教条,而是与实际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与实践的这样的结合,思想才可能指向正确的方向。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刷屏的关于拉姆的文章,说到基层的不作为,公权力的缺位,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就是长久以来去组织化、去政治化之后的中国的现实。一方面科层化的组织不仅不缺,反而更为庞大、冗赘,而另一方面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充满能动性的政治则荡然无存。当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工作消失的时候,个人(或者家庭)就只能自己承担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的灾难性后果。
由此也说到曹老师的第十一篇,此篇是对他自己“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做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其实我觉得曹老师“把现代性定义为——时间的、空间的、学习的、向下的、实践的”挺好,既是他个性化的语言,又有中国革命在其中的特定内涵。而曹老师不止步于此,认为革命的现代性还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他将其概括为“可以把中国革命的进程看作人的觉醒过程,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价值”,这一概括却让我心有踟蹰,不能完全赞同。
因为“人的觉醒”,其实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标榜的口号,西方如此,中国亦然,我们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里面就有一个“人的发现”,这当然也是人的觉醒:以独立的、自主的、进步的人代替封建制度下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人。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比这个更进一步(也可以说更具有现代性),在于它要完成“阶级的觉醒”,这里面不仅包含了人道主义,而且超越了人道主义。就像在发动农民的过程中提出的“过去当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人”,是要摆脱奴隶地位的、像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而且,这个“人”,还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要意识到自己是阶级当中的人,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打碎阶级的锁链,推翻被压迫、被剥削关系的,就像曹老师第十二篇所写——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在改造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政权和新的人。
我当然不是说曹老师没有“阶级的人”的意识,因为他通篇都在强调阶级路线。我也不是说曹老师把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嫁接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人的觉醒”上,因为他的思路是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中国化上。
然而在此篇中曹老师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的一个例子,想要说明的却好像是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论。“人是能动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劳动是人的劳动而非工具的劳动”——这个判断不像是来自于《哥达纲领批判》探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时对平等、不平等权利的说明,而更像是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对“人”和“劳动”的说明。
类似这种“个”与“类”,“本质”与“异化”,“价值”与“工具”……的讨论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启蒙学说中都并不鲜见,像康德也提出过“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马、恩成熟时期的思想、以及在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精髓是什么?其实曹老师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都已经谈到了:革命的阶级路线,革命依靠谁,为了谁,革命的无产阶级化……
在否定革命现代性的潮流中,经常拿来用的就是审判革命中断了“人的觉醒”,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曹老师此篇认为“人的觉醒”是革命的更深层次的现代性。我倒是觉得,“阶级的启蒙”涵盖了“人的启蒙”,“阶级的觉醒”包含了“人的觉醒”,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可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来却完不成的任务,并且能够完成更高一级的实现。
由此说到曹老师的第十二篇,“现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是资产阶级领导不了,才必须由我们无产阶级来领导。”
文后有一个留言很有意思:“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井冈山开始的”,这种简单的类比很容易流于表面的相似,如:都是“分田”,都是满足了小生产者的积极性……然而两次分田,进步与否、意义如何却是大相径庭的。
如果将起于井冈山,成熟于1940年代后期的分田称为第一次分田,那么这次分田面对的是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使广大农民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所以它是有进步意义的。而197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分田,面对的是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土地本来就是大家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收益也属于全民,然而这时候却重新恢复个体生产,可能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欲求和积极性,但却是开历史的倒车,导致了后来的层出不穷的“三农问题”。
前一次“土改”,无产阶级领导完成资产阶级完成不了的任务,第二次“土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退回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另外,还因为看大家的文章引出来的一些疑惑,也想在这里谈一谈。
曹老师的文章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认为“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核心理念就是‘工具’理性,它的逻辑起点和制度设计,都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对待”,而人的工具化,在中国古代也一样,“这些理念恰恰与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统治术不谋而合”,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则反其道而行之,“革命要革掉的,恰恰正是这些以人为工具的各种微观的管理规则和宏观的政治法律文化”。
总体的判断我没有异议,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抑或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其实都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体现。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会说我的逻辑起点和制度设计就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榨取人,不会,它会说我的一切设计是为了人,为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儒家也不会说我要使你成为非人,它会说我的一切设计是为了你更像人,成为君子,仁义礼智信集大成,天人合一天下大同……
这些都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只不过,在现实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却是价值理性难以实现,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这种悖反之所以产生,究其根本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有资本、有劳动力市场,就会有剥削、压迫,有无底线竞争,有人被异化为工具;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有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就会有地主、有官僚,有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说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真的“是价值理性战胜了工具理性”的话(我还是觉得这样的概括很不马克思主义),那么它其实是把“价值”建立在了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石之上,而非只有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约言”。
我的疑问在于,即便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工具化”的现象也并非没有,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说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脱胎于资本主义的母腹,它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也可以说现实条件还没有成熟到挣脱一切束缚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类似列宁或毛泽东提出的“要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是怎么回事?是工具理性吗?做资本主义机器上的螺丝钉与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有何不同?
另外一个问题,在黎老师分享读后感的时候,举了一些文学作品的例子,很生动,如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来说明中国革命中产生的另类现代性。小二黑和小芹反封建、反家长权威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成为可能?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私奔等传统结局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革命、土改。因为这两个年轻人不再需要他们的家长给他们生活资料,不怕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里有一个强大的生产资料再分配的动力,使得二人的爱情不至于成为一个悲剧。”
这个看法很有趣,以前我们常说新生的民主政权带来改变,两个年轻人成为不同于老式农民的新一代,敢于追求,敢于反抗。而黎老师则点出了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带给年轻人的反抗的基础和底气,很有启发性。
我自己在读《小二黑结婚》的时候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是革命政权里面也有坏干部,像金旺、兴旺兄弟俩,在基层政权中占有位置,小二黑和小芹最终赢得胜利,是诉诸于更高一级的区政府主持公道。应该说赵树理还是非常敏锐的,不回避新政权也可能被旧势力把持,但解决方式则有点老套:更高一级的、更大的干部是明察秋毫的。所以这里面依旧有一个困局:要是更高一级的干部也不好怎么办呢?革命文艺很少触及这个困难,一般都会是上面派来的代表党的正确领导的干部来解决矛盾和问题。
因此,在现实当中,哪怕是在革命进程中,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任务都不是像在革命文艺中那样得到彻底、完满的乐观解决。
用一句来概括就是:一次革命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未来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