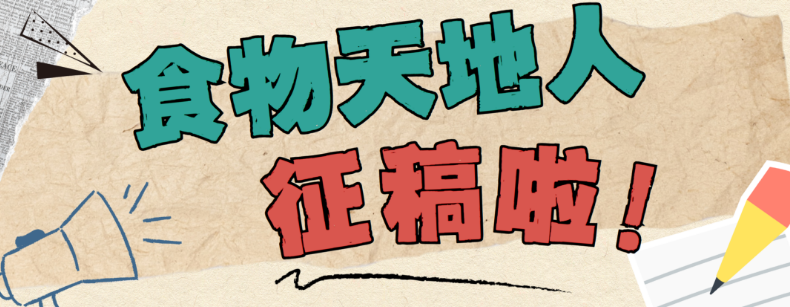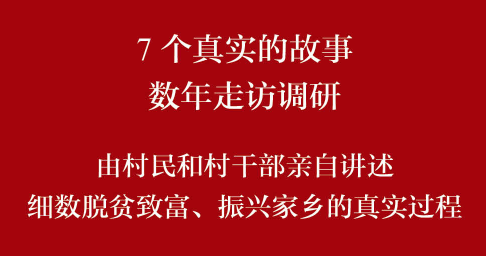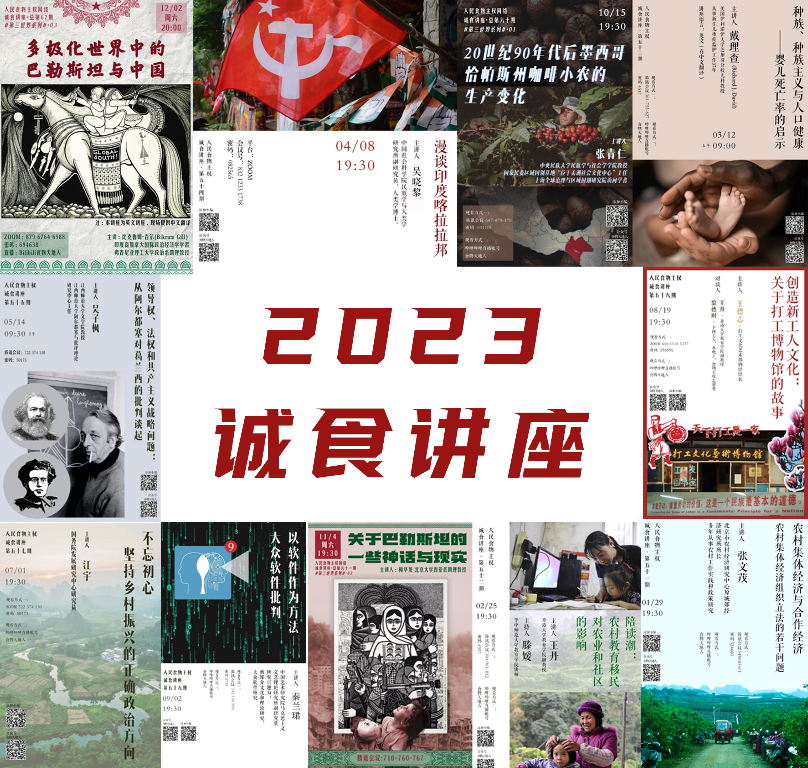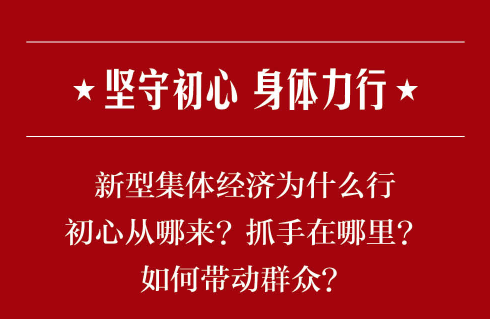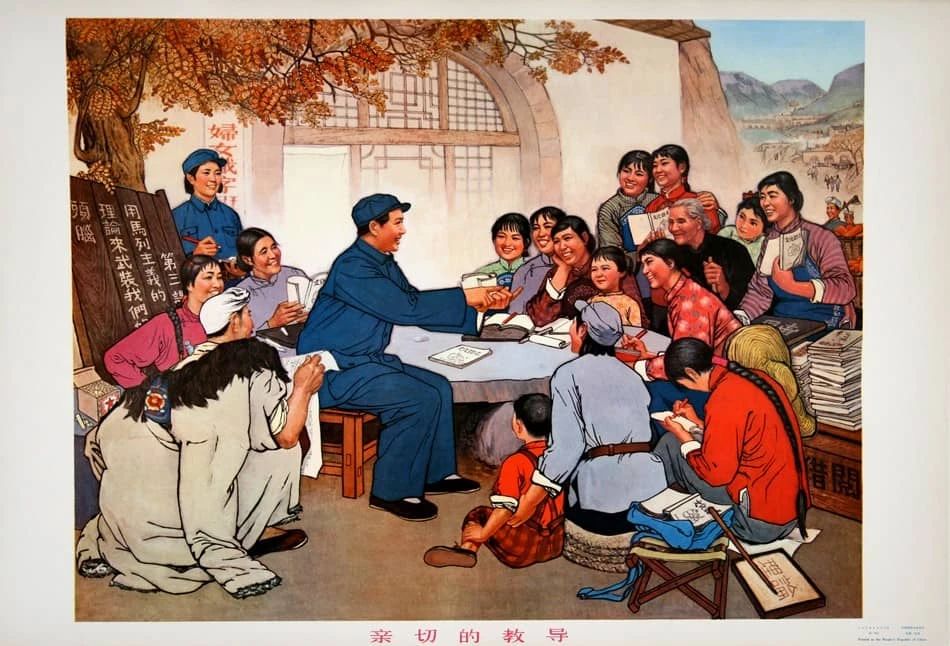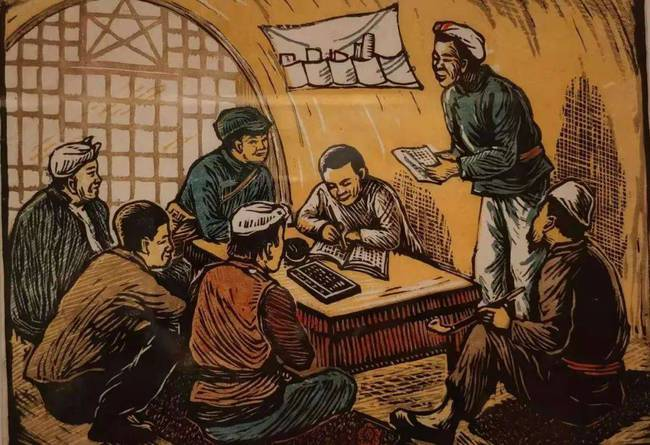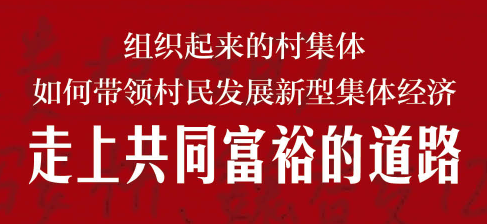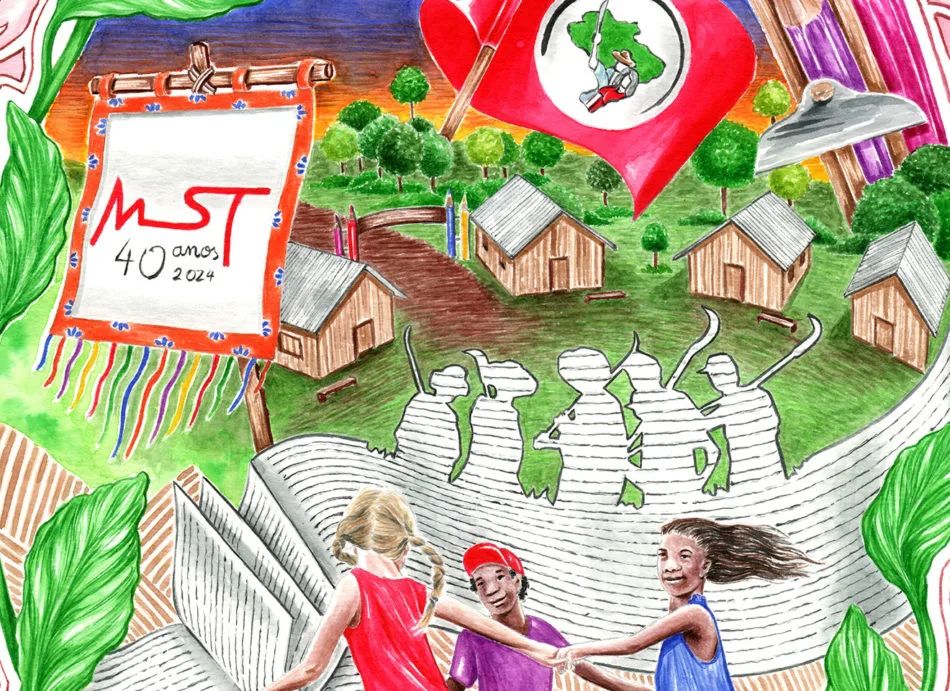诚食讲座 | 徐于楠:全球农药的变迁和中国角色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5-08-21 阅读:1016 次
导 语
农药残留已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严峻问题,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研究显示,2002至2017年间,我国发生的562起农药中毒事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由蔬菜、粮食和水果中的农药残留引发的。然而,当食品安全事件爆发时,舆论往往简单归因于生产者滥用农药或检测机制疏漏,这种片面指责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农药所招致的环境和健康危机是全球广泛存在的问题。农药的推广与使用根源于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全球农业化工资本息息相关。一方面,单一种植、追求高产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使农业生产不断加深对化学品的依赖;另一方面,农化资本通过转基因技术等,绑定种子与农药,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产。而中国的变化则更是惊人:八十年代,中国农药使用量和出口量都居于低位;短短40年后,中国化工企业跻身全球十大农化企业之列,中国跃居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原药生产基地,中国农药使用量也居高不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巨变和与其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呢?
本次诚食讲座中,徐于楠老师引入全球视野,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梳理了我国农药生产业的发展轨迹。她的研究清晰地揭示出:农药的问题,远远超出农民素质或者制度监管的层面;市场和农化资本才是真正操控农业生产和大众健康的隐秘的手。
主讲人|徐于楠: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农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农政研究主要概念栏目编辑。其研究聚焦于食品政治与转型、农村发展与农政变革、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变迁,以及农村生计问题,尤其关注中国与全球发展的互动关系。
文字整理 | 火云、竹节虫、笑的风
责编|决明、云岫、侯鼓
审核 | 徐于楠、御寒
后台排版|童话
大家好,我是徐于楠,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全球农药的变迁和中国的角色。本次分享主要基于我和陈义媛老师合作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上,是一篇比较概念化的综述类文章。目前我们关于这个选题的探讨还处在比较初始的阶段,起初我很纠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阶段和大家做分享。后来想了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现在跟大家分享,以概念化的角度来探讨目前相关知识领域的空缺,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探讨和研究,也许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研究缘起
关于这个研究的起源有一个小故事。最初我准备博士研究的时候,这并不是我的主要课题。我跟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博士生同学,当时特别想一起合作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在俄罗斯跨境种地的研究,然后我们各自分头找材料。我找中文的,她找俄罗斯的相关报道和文献,汇总讨论之后有了很意外的发现——在中文报道里,很多中国农民称他们去俄罗斯种蔬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难题是需要大量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因为当地的法规更加严格。

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种地相关报道截图|图片来源:讲者PPT
比如这篇今日头条上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在俄罗斯种地的农民,他的大棚常年雇佣三四十个中国农民,而他之所以雇佣这么多人,是因为俄罗斯对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和检查,他们的农药以及化肥的使用量只有中国的1/5。而当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就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生产。
俄罗斯的检验检疫机构在取样前不会和农场打招呼,他们会去棚里直接拿产品、土样、水回去做化验,看有没有重金属超标和农药残留,如果不合格,农产品就必须下架。早些年,不少中国农民租种俄罗斯土地进行农业经营时,还按照国内的习惯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结果被俄罗斯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后来这部分农民自己用微生物菌肥又当农药又当肥料,病害减少了,产品品质提高,也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
我的俄罗斯同学查找的资料又勾画了另外一幅图景。俄语以及英语的报道反映,当地的居民声称来自中国的农民比当地农民在种植中使用了更多的农药化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很多俄罗斯男性酗酒成性,对农业工作缺乏热情,但他们却反过来抱怨中国人起得太早,化肥用得太多,把土地榨干了。一位愤怒的本地男性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块由中国人耕种的田被灰蓝色的粘液覆盖,据称是化学品残留和灌溉工程失败所导致的。
这些跨境去俄罗斯种地的很多都是农民,并不是大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农药使用超标的问题呢?虽然这个研究后来没有进行下去,但是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世界粮农组织(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发布的资料中有一项数据是关于农药使用密度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农民的农药使用密度是2.63千克每公顷,同年俄罗斯农民的农药使用密度是0.32千克每公顷。二者差距巨大,这是为什么呢?在农政研究中,大家可能会认为,农民尤其是小规模种植的农户倾向于更少使用农药化肥,但中国农民为什么会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呢?这个疑问促使我开始了这项研究。
接下来,我将先梳理中国和全球农化产业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而后总结目前学术界对农化产业研究的共识,以及相关研究的缺陷。
二、研究背景
首先说说我们的研究背景。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总结了当前农药问题研究的认知现状及其局限性。为弥补这些不足,我们对中国农药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这就是本次我要讲的主要内容。
下图是一个关于全球农药使用量的数据。1990年到2020年间,全球农药的使用量增加了约90%。需要注意的是,粮农组织的数据收集并不完整,缺失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所以这个增长幅度很可能是被低估了,但即使在被低估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这个增量是非常惊人的。

1990—2020年全球农药使用量数据表|图片来源:讲者PPT
关于农药使用的重要性,学界一直有很多讨论。有些人认为农药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帮助农民在更少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的粮食,保护粮食作物不受病虫害以及杂草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不使用农药,水果产量可能会减少78%,蔬菜产量会减少54%,谷物会减少32%。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这项研究是基于全球粮食缺乏的假设,但是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粮食缺乏(粮食产量低)的问题,而是出在了粮食分配上。
抛开农药重要性的不同观点,农药的使用确实带来了环境和健康方面的风险。现在全球有64%的农业用地存在农药污染的风险,在欧洲大概有1/3的谷物制品中检测出了农药残留。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测实物样本中,有一半都含有农药残留。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化产品如何使用、使用量多少、以及由谁控制这一过程,这些关键问题跟全球粮食体系的未来以及全球健康息息相关。这里的全球健康包括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等维度,因此,深刻理解全球农化体系(global agrochemical complex),探索一条通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复杂的全球农化体系当中,中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的农药化学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以及最主要的消费国(可能是最大的,但因为全球数据的不完整性,所以并没有能够确认是不是第一)。同时中国企业在全球农化市场中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通过下面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和2020年全球农化市场的变化,全球十大农化公司里面有三家是中国的企业,而且他们加起来大约占了全球市场份额的30%。所以说了解中国农化产业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以及中国在全球农化市场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前十大农化公司在2009年与2020年的变动情况 | 图片来源:讲者PPT
我们对中国农化产业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梳理,目的是了解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情况。通过总结1990年至2023年在知网和web of science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影响中国农药使用的因素上。这一类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农药的使用归因于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变量,例如,有20多篇文章研究了农场规模和农药使用之间的关系。有的文章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土地整合和农场规模扩大有助于减少农药使用,同时推动中国农业的转型。还有一些研究从管理创新角度着手,例如农产品的认证,农业保险合作社或者技术创新(如转基因棉花,生物防控技术)对农药使用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解释往往过于单一或者简化,忽略了农药使用背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权力关系,例如国家政策如何运作,市场如何影响农民的选择,以及企业在这个体系当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因此解释力度有限。

中英文文献研究因素对比表|图片来源:讲者PPT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聚焦于中国农药使用现状,主要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研究展示了中国农药使用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趋势,以及相关政策的演变。微观层面研究更具体,例如,有一项在村庄层面的民族志研究关注了农民对农药依赖的问题。另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农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但是这些研究不足以全面覆盖中国农化体系,忽视了其复杂性,也缺乏一个全球视角。全球视角是指中国的农化体系与全球农化体系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如果单从国内这一个视角来看,很难理解这样一个跨国多层次的复合系统如何运作,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之中。
总体来看,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当中,中国农化体系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被忽视了。在历史维度上,相关分析显得比较零散,没有系统性。在空间维度上,忽略了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相关产业之间的联动。所以我和义媛老师在研究中,先对中国农化产业的发展轨迹做了一个简单的历史性回顾。
三、中国农药发展历史
中国农化产业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在这个阶段,农药的使用量和出口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上升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农药使用量持续增加,但是出口仍比较有限。扩张阶段是2000年初至2010年初,这一时期,农药的使用量和出口量双双增长。重组阶段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农药的使用量开始下降,但是出口量波动不定。



中国农药发展阶段及使用量、出口量变化图|图片来源:讲者PPT
全球层面来讲,在初始阶段,整个农化产业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主导。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药相关政策文件表|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上升阶段,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得农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替代性作用上升,带来了农药使用量的显著增长。从供给端看,中国的农药市场也逐步走向市场化,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正如我在上面这个表格里面总结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农药行业,一个多元化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
在这个阶段,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研发投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研发重点集中在如何用更低的成本制造农药,以及在现有非专利的活性成分的基础上开发新配方,而不是开发新的活性成分。换言之,不是进行专利研究,而是在非专利覆盖的活性成分的基础上进行新配方的研究。
同时在这个阶段,有很多全球性的农化巨头,例如先正达、拜耳、杜邦都开始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这些企业纷纷建厂的考量包括三方面,一是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二是环保监管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较为宽松;三是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对他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到了第三个阶段,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在供给端,大量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了中国的农药行业;在需求端,中国农药市场迅猛发展。我们总结了五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农药价格的下降。21世纪初国际大公司的农药专利陆续到期,技术创新放缓,廉价的仿制品迅速占领了市场,使得农药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短缺。随着农村人口不断流出,农民越来越依赖化学手段来省工增产。同时,进城务工带来的工资收入也反过来促进了农化产品的消费,回家务农的时候,农民将在城市获得的收入用于购买农药和化肥等农资。
第三个原因是土地整合政策的出台。2008年国家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明确提出了推进中国农村土地整合,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由大户集体或者农业公司运营的大农场大量出现。这些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往往是单一种植,它们遵循标准化和产业化的经营方式,这类经营方式对农药的依赖程度会更加高。
第四个原因是饮食结构转型。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转变,对蔬菜、水果、棉花等作物的需求不断上升,这些作物的农药使用强度远远高于粮食作物,耕地使用从粮食转向经济作物,也是这一阶段中国农药使用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个原因是本地化的农药销售网络的推动。在集体化时期,中国的农药销售体系是基于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随着商品化的过程,这些农业技术推广站就演变为了更加深入基层的本地化的销售网络。县乡级的零售商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农民,他们会聘请村里的一些能人做业务员,直接在村里推广农药。此外这些销售商还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培训,传播农药的使用方法,这种知识传递在基层有效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知识体系,推动了一些对农药依赖性耕作方式的构建,也加剧了中国农村对农药使用的依赖。
在这一阶段,除了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生产的大量农药也用于出口。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农药的出口迅速增长。这个背后主要有三大原因:中国低廉的生产成本跟劳动力成本,相对宽松的环保监管,以及比一些发达国家更有利的税收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廉价农业活性成分(例如草甘膦,又叫除草剂)供应国,在国际农化市场当中占据了一个关键的地位。
第四个阶段是重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更加重视环境的可持续性。尤其是2000年后多起食品安全危机爆发,推广绿色农业逐渐被提上了政策日程。在绿色转型的大趋势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
2015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双行动”,随后在2017年又推出了更加严格的新版农药管理条例,对农药的登记、生产使用和流通等环节进行了更强的监管。这一系列由国家主导的绿色转型,其实也可以部分看作当前中国农化企业在世界的产业链中寻求升级的努力,由过去的廉价活性成分的供应国逐步转向为一个高附加值的制剂研发者和制造者——廉价活性成分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会比制剂的研发和制造要更高。

21世纪10年代中期后中国农药相关政策文件表|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这一阶段,一些国际农化巨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仿药企业的加入导致的激烈竞争,这些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低,生产的农化产品成本会更加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化巨头遇到了高昂的研发门槛和创新壁垒所带来的压力,例如环境政策带来的研发成本增加,导致研发放缓。

2009年与2020年全球前十大农化公司变动情况表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农化产业当中逐渐走到了前沿,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从上面这张表格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企业(包括国企),通过并购在全球的农化市场当中起到了非常主导的作用,同时,这些农化企业在中国整个农化市场产业链的升级——从廉价的原药生产者到制剂的研发和生产者的转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除了市场重组之外,中国农药产业的发展亦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和转基因政策调整的持续影响。这些变化将对中国农药产业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初步探讨。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药等商品的贸易,增加了贸易频次,加强了贸易联系。

2020年中国农药出口前十大目的地国家及出口量占比表|图片来源:讲者PPT
观察上面这个数据图表可知,印尼、阿根廷、泰国、俄罗斯、越南和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已成为中国农药出口的目的地。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药出口的发展,中国农药的出口也进一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这是一个相互重塑的过程。我们观察到,许多拉美国家的农民迫切希望获得中国生产的廉价农药——因为此前欧美农化巨头生产的农药成本过高,中国生产的相对价格低廉的农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生产中的困难。此外,中国的农化出口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使用过程也产生了影响。
同时,在转基因种子的发展方面,中国的路径与许多国家存在差异。在其他国家,农药销售通常与特定的抗除草剂转基因种子捆绑,但在中国,过去农药的增长与转基因种子的关系并不紧密。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政策规划,中国采取的路径是:先推进非食用作物转基因种子商业化,再拓展至间接使用领域(如饲料),最后才是直接食用作物的转基因种子商业化。2020年之前,中国唯一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种子是抗虫棉(即BT棉花)。
2021年,中国启动“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明确了推动转基因种子的研发和推广。此后,包括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在内的多种转基因饲料作物陆续获得商业化许可。这表明在中国,抗除草剂转基因种子可能会被广泛推广,进而对中国农化产业产生重塑作用——某些品牌除草剂的使用度可能大幅上升,这不仅将重塑中国国内农药行业,也将对全球农药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回顾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视角无法全面深刻地描绘出中国农化产业的发展轨迹和结构特征。中国的农化体系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根源,它并非一个自我封闭、自我维系的系统,而是嵌入在更广阔的系统之中。历史上,中国的农化体系嵌入于中国农业社会转型过程;在互动层面,中国农化体系既受全球互动的影响,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农化体系发展。
农化体系本身与种业、粮食体系等多个领域紧密相连,因此,要填补知识空白、理解中国农化体系的复杂性和演变路径,需要更全面的分析框架,需从历史、互动和动态关联性的角度进行解读。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听到大家的反馈与想法,谢谢。
四、互动交流
问题1:徐老师在讲座中提到,2015年之后中国农药使用量有所减少,未来是否会持续减少?若使用量减少,农民在农药方面的支出是否也会相应减少?这是基于您讲座中提供的趋势提问。
徐于楠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尝试回答一下,因为我与许多人一样也在探索当中,分享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供大家讨论。
首先,中国农药使用量减少,未来是否持续减少?我认为这与国家的绿色转型政策有关。但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角度看,中国农村农民的种植过程中,农药使用增长与农民的使用习惯和知识体系变化密切相关。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除草、除虫、施肥,农业知识通过口口相传的经验累积。但中国传统耕种方式已发生变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这推动了农化产品的使用,使其成为替代劳动力的必然选择。
关于未来农药使用量是否持续减少,取决于劳动力替代问题及价格因素,而价格因素又取决于市场变迁。一方面,劳动力替代问题在于:若不使用农化产品,将由什么来填补劳动力空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根源在于劳动力问题。另一方面,若劳动量使用减少,支出是否减少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支出不仅取决于使用量,还取决于价格因素——这取决于整个市场的变迁。在一个商业化的环境中,价格是否低廉与竞争者数量相关。但市场一定是趋向聚合的,当聚合化(concentration)程度高(即少数企业垄断市场)时,未来支出是否减少,取决于价格变迁以及市场是否形成少数企业垄断的条件。
因此,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政府也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很难简单回答“会”或“不会”。
问题2:您在讲座中提到了中化收购先正达的背景、脉络和用意,能否再详细讲解?
徐于楠
感谢提问,但这个问题超出我的专业范围。我并非企业人士,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处于资料收集阶段,资料来源包括网络新闻及一些其他研究者对先正达的理解,未对中化或先正达进行访谈,因此难以深入分析中化收购先正达的背景、脉络和用意。您提到的“用意”是指先正达的用意、国家的用意,还是对全球农化市场变迁的影响?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很复杂。
但众所周知,先正达是国有企业,整个收购过程备受关注。浅谈“用意”,我认为可能与中国绿色转型有关——收购或许与中国希望从廉价的配方原药生产国向制剂创新和制造者转型有关,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具体情况需更多研究和访谈才能得出结论。
问题3:不用化学农药除草剂的替代方案,能否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保障食品安全?
徐于楠
我并非技术背景出身,更关注农化及经济变革。关于替代方案,目前我看到一方面是大规模使用生物制剂,另一方面是回归传统(即生态种植)。我们需要农化品,是因为传统生态链被打破——单一种植方式取代了传统生态链,导致需投入元素补充,且单一种植更易引发病虫害,形成“问题叠加”。在我们领域,也观察到了一种叫“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的现象,即技术将整个种植过程锁定,导致如今的种植模式。但是否有可能回归传统,即打破技术锁定,回到传统种植方式?同时,在生态种植领域,又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涌入,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为了食品安全,还是资本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引发的新一轮投资热潮?这些都值得思考。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有关注关于“有机标准”“环境友好”等标签的探讨。在当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环境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距离,这种距离导致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与恐慌,因为他们看不到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关系被割裂。不信任机制引发了消费者对生产过程的怀疑。标签的出现旨在揭露这种距离和生产关系,以透明化的方式解构生产过程,但也让消费者额外支付购买。从某种角度看,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相反:商品因隔离了社会使用关系,让消费者看不到剥削或环境变迁,可毫无负担地购买;而如今,对环境和农民公平价格等道德层面的担忧,促使标签兴起,却反过来引发另一种“拜物教”(如环保拜物教或“漂绿”(green wash))。
抱歉讲得有点多,可能偏题了,主要是想提醒:需探讨新型农药究竟是为环境考虑,还是资本涌入的途径。
问题4:徐老师PPT中提到,在2015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的行动计划,政府通过哪些手段减少农药使用?具体政策工具库是罚款、补贴还是其他?您是否有相关政策研究可分享?
徐于楠
根据我对政策的解读,政府多通过补贴和培训等手段推动更环保农药的使用,例如补贴新型绿色农药,通过经济手段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具体情况需进一步实地研究才能更全面回答。不知义媛是否有更多补充?
陈义媛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关于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政府目前的手段,据我零星观察:政府可能在农药的生产方面做了一些管理,但从市场销售和农户使用情况看尚不明显,农药销售层面几乎未受影响。我近年关注全国不同地区农药化肥销售情况,不同层级代理商、销售商的日常经营几乎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他们知晓政策,但经营无太大变化。
“零增长”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如刚才徐老师说的,大部分是以项目的方式开展。例如一些地方实施“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项目,地方政府可能会设立示范区,推动生物农药、有机肥使用。但并非完全禁止使用农药化肥,而是以生物性的替代农药和有机化肥来代替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补贴对象通常是示范区内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公司等,通过为他们提供补贴,鼓励他们使用上述替代产品来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此外,有朋友在聊天框里提到了“统防统治”,这在很多地方对减少农药化肥使用也产生了帮助。但目前来说,能真正做到“统防统治”的主要是大规模经营主体(如公司),他们通常有比较大范围的土地。组织小农户开展“统防统治”存在很多挑战,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细碎化、农户种植的分散化,“统防统治”的协调难度比较大。很多卖农资和做社会化服务的主体想尝试,但主要还在探索阶段。
目前,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仍限于小范围试验示范。关于是否真的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存在争议。我们看到一些国际上的研究,专门对比了不同来源的数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有减少,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似乎不完全对应——FAO数据显示中国农药化肥使用量未明显减少。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仍存争议。
在农药生产方面, 2015年之后,农药生产量确实下降了几年。但到2017、2018年之后,生产量又上去了,这主要是因为农药出口量的增加。中国生产的农药大约只有20%的在国内使用,80%都出口了。我认为,这个政策提出的时间还不算太久,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嘎 嘎
想问问老师是否有关注一些符合“有机”标准的、环境友好的新型农药?刚刚徐老师说在关注有机标签,我比较激动,因为我也在关注。
继续刚刚聊到的农药化肥减量话题,我觉得现在行动的方向,不是从生态种植的角度去减量,而是使用更加“生态”的农药化肥。所以,这种“生态”的农药化肥可能没有被统计在官方数据中。它的使用量可能并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种不在已有定义中的农药化肥,才实现了数据的减少。这是我的一个猜想。
确实现在很多生物制剂公司正在该领域加大研发力度,包括和高校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但我之前访谈的一些生态农人,他们对市面上或政府提供的有机肥的质量都表示怀疑,觉得用了不太对劲。这种替代性的农药化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更多调研。这是我对前面讨论农药化肥减量的一些联想。
关于有机标签,确实像徐老师说的那样,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环保拜物教”。不只是有机标签,还有其他很多标签,已经形成了一个“可持续标签”的市场,比如可持续渔业认证等。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消费者眼花缭乱,不知道该信哪个标签。甚至需要再来一个第四方给第三方做认证,而这样的认证可以无限地传导下去,我觉得挺荒诞的。本质上,它是通过认证的方式凭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体系,除了标签市场,还有一个认证市场,由业内很多检测机构、认证公司及认证人员构成。在这里,公众的信任是一个可以花钱购买的服务。而由于有机认证的高价格,就事实上很多生态小农排斥到了这个市场之外。
说到这里,关于标签,我想在消费者维度之外补充一个生产者的维度。虽然现在国内还没有规定“生态认证”的法律法规,所以大家还可以用“生态农产品”来销售。但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是一定要求认证才能用这个名称的,而且费用动辄上万元,具体我没有专门去了解,但确实很贵,而且每年都要重新认证,对小农户非常不友好。
所以认证一方面抬高了有机食品销售的门槛,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导致了异化,即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农户为了拿到认证,不再是用自己认为生态友好的方式生产,而是为了符合认证标准去生产。这个过程中,生产者可能只要能达到标准就不管别的了,比如“只要检测不出来,稍微用一点农药也没事”;或者送检时,拿自家一小块确实没用农药化肥的地里的土和作物去检测,但一起卖的其他作物还是常规种植的。这里面有猫腻的空间,我也听到不少生态农友的批判。
我觉得背后最核心的问题是,无论是新型的生态农药制剂还是传统的,都没有让农民自己的知识发挥作用,不能提高农民本身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还是在使用购买来的商品解决问题,而不是运用自己的传统智慧,或在因地制宜的过程中试验出来的方法。
所以我认为,这种新型农药制剂也许可以发挥一定的补偿或者过渡作用,但能否作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我是存疑的:科技总有很多未知因素。比如植物基的生态农药,虽然有易降解、低残留的有点,但也被发现对其他生物有毒害。比如苦参碱对鱼类和蜜蜂有较强毒性,除虫菊素对猫毒性高。因此,我们也很难保证这些现在看来所谓环保的制剂,以后不会被发现有新问题。我觉得食物主权网络倡导的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应该是更值得探索的方向,从顺应自然、社会规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这样更加可持续。
徐于楠
我觉得嘎嘎刚刚说得特别好。我想回应一下,关于标签和什么是真正的有机,学界有很多探讨。一些批判性研究指出,在很多国家(如美国)出现了一种叫“industrial organic production”(工业化有机生产)的现象。它只是从技术上达到了有机标准,为了标签而生产。但本质上,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往往只保证这一小块土地的环境,却对周围的劳作关系或更大的环境起到了破坏作用。它没有瓦解工业化单一作物生产模式,只是从技术上减少了化学产品的投入使用,但它可能会用其他东西替代,并不一定更绿色环保。
阿 菜
我首先给大家念一段我最近参观的博物馆的展览介绍:
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的农作物之一,早在近万年以前,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粟的种植。2001年至2003年,考古人员在对赤峰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中,通过浮选法选取了1500例经过人工栽培的碳化粟和碳化黍,经检测鉴定,这些谷物距今约8000年,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了约2700年。这一发现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表明粟作农业也通过北方草原通道,自东向西传至欧洲,奠定了赤峰市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旱作农业起源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我为什么要念这段?因为它跟我最近的一个小故事有关。前段时间我回国,爸妈煮了小米粥招待客人,他们还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在国外买的小米——其实这是我在赤峰兴隆洼那边一个合作社买的小米,是有机种植的老种子,味道很好——家里的客人就说:“肯定是国外的东西好,都没有打农药。”我当时就反驳,这是我们中国北方的有机小米,不是国外的,而且国外的东西也打农药。
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说我们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从小到大,很多人都说日本、以色列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最发达、最生态,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刚才徐老师分享的图表以及FAO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以色列、韩国这些最发达的国家,包括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化学品使用量都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多。但这些迷信很难一下子打破,所以才有人会觉得国外的小米好,因为“没打农药”。但我们都忘了小米的根在中国,而且我们的耕作历史比其他许多文明要早很多年。
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一直有这种对西方的迷信,我们是不是被西方的标准和话语影响太深?以我个人在法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为例,我曾在葡萄园打工。七月份最热的时候,我们早上四点起床,去把葡萄藤拉直、扎起来、摘掉叶子,好让葡萄长出来。这期间,我们每天至少要用掉两三副手套,因为葡萄园的农药太多了。在葡萄园工作的那段日子,我的鼻子最难受。最近一项科学研究证明,到2030年法国胰腺癌的发病率会非常高[1],因为法国使用的农药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这些农药去哪了?我猜想就在葡萄园里。所以很讽刺的是,中国一些中产阶级喝着法国进口的红酒,觉得是高档和品位的象征,但这些葡萄酒里充满了农药。
法国已经没有自己的有机生态土壤了。法国的有机农人如果想种有机作物,需要去东欧国家买土壤。这等于是把自己国家的土壤污染了,不去治理,反而去别的国家买土壤,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掠夺。最近还有个新闻,日本科学家在某些城市的雨水中检测出了超过90%的啶虫脒农药[2]。很多人还以为日本的农作物非常生态,其实不是,它的农药用量比中国高很多。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是,我们要破除“西方农业比中国更好”的迷信。
第二点,我们要破除对技术和“绿色革命”的迷信。我们常说的绿色革命,其实是跨国资本的操作手段,它的“绿色”根本就不是绿色。包括刚才嘎嘎和徐老师都讲到的新兴生态农药,有时也只是在这种迷信上贴了更时髦的标签,是“新瓶装旧酒”。比如现在有一种杀虫技术,不用传统的杀虫药,而是用基因沉默技术(RNAi)。这种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技术,其实它杀死的不仅是目标害虫,还会杀死与目标害虫基因有70%~80%相似的其他昆虫。
现在这样的技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AI可以自己做很多RNA和蛋白质的模型演化。所以,基因技术加上人工智能的操纵,其技术危害会越来越大。作为一个技术批判者,我认为这是技术在助纣为虐。大家需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比如对病毒靶向农药等。人工智能会使我们科学家现在搞的转基因技术变得更恐怖。而且AI本身的问题,比如幻觉(hallucination)或黑箱效应,都会导致未来通过技术解决农业问题的风险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
第三点,既然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和对技术的迷信,那什么才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合作和团结。在如今气候变暖的危机下,没有一个农民可以单打独斗做一辈子,他会碰到很多压力。现在西方的一些小农也开始寻找团结农业的模式,比如不同地方的农民聚集起来,互相分享农业知识和工具,否则他们无法在当前情况下单干。
我们以前有很多成功的合作社经验。现在,我们如何在这种环境下重新构筑一种团结的、集体的合作精神?这可能才是真正面对未来农业危机和气候危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侯 农
接着阿菜刚才说到的农业的初衷是团结和互助,这让我想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农化问题,其背后都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一方面,就像徐老师在一开始研究背景部分讲到的,有人觉得不使用化肥农药,粮食产量就会下降,带来饥饿。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说使用化肥农药不是因为产量不足,而是分配问题。如何解决这种悖论?食物天地人公众号推送过的《乡村纪事》这本书讲了中国现在集体经济的一些实践,这些实践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编者注:《乡村纪事》节选 | 塘约实践:靠外部资源还是内生力量?;藏北高原上的牧业公社:如何创造安全感、获得感、可持续性 | 《乡村纪事》节选;大坝经验:山沟里的移民村如何复刻华西经验? | 《乡村纪事》节选】
现在探讨生态农业,大家总会想是不是要回到小农生产,即以家庭为单位,自己一小片地,多样化种植的生产体系。但实际上,如果大家去阅读《乡村纪事》这本书就会意识到,以村庄或更大单位的集体组织方式,其实更适合生态化生产,能把生态农业真正落到实处。更大尺度上的互助团结,可能是未来解决农化问题的一条可行出路。
徐于楠
谢谢你们的分享,我也学到了很多。
关于技术中心主义,即“技术万能”(technology can solve everything)的观念,学界已经有很多批判。出于对这种观念的批判,目前有一种思潮认为技术是双刃剑,有好有坏,有时副作用甚至超过正面作用,需要客观地看待。而一种更激进和批判(critical)的观点则认为我们人类社会陷入了一种叫“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的境地。(我不知道我的翻译对不对。)
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是被技术锁定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就用新的技术革新去解决。比如,为了大规模生产,我们先搞规模化种植;后来有了病虫害,就用农药化肥;农药化肥效率不好,就提供更好的喷洒技术等等。这一步步的过程,就是刚才提到的常规化(normalization),或者叫技术的日常化,这个过程让大家觉得技术的使用非常自然。我们就这样一步步被锁定(locked-in)在这种关系里。这可能是对技术一种更加批判的认知。
参考资料:[1]https://www.sciencesetavenir.fr/sante/cancer/mystere-francais-l-explosion-du-nombre-de-cancers-du-pancreas-semble-lie-aux-pesticides_183306.amp
[2]https://www.unaf-apiculture.info/il-pleut-de-lacetamipride-au-japon-et-cest-tres-inquietant/